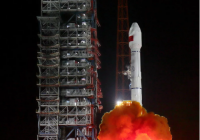成都商报消息,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六,宜归家。
在翻看一本老黄历后,唐永柏决定这一天回家。过去15年,他一直待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背一根棒棒谋生。他早已熟悉这里的生活,但又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了,毕竟,再过两天,就是他76岁的生日。
一个多月前,一段“重庆最老棒棒”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唐永柏在视频里说,当棒棒“自由,但挣不了多少钱”,他磕着烟袋,眼神里有倔强和无奈。纪录片《最后的棒棒》讲述了重庆棒棒从业者逐渐消失的故事,导演何苦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时代变迁,他们的背影无法挽留。
11月4日中午,唐永柏回到了自己在遂宁市蓬溪县常乐镇的老家。唐永柏不愿去养老院,他还是想住在村子里,住在家里。
最后一天
跑了两单挣了25元,把棒棒交给老板
11月3日,唐永柏见到熟人就打招呼,“明天就回去了”,他说过两三年再来重庆看看。他的熟人不多,都集中在菜园坝火车站附近,同样扛着棒棒的几个上了年纪的人,以前的雇主吴老板,托运门市的彭老板。有两笔账必须要还,他找朋友“周伯通”借了150元,是大半年前自己看病时借下的,“周伯通”再三没要,他又颤抖着手把钱揣回口袋。前两天他吃了一碗米粉,4元钱,当时身上没钱,他把钱交给托运门市的彭老板,请对方代为转交。
在重庆的最后一天,他没有闲下来,上午帮人搬了两趟箱子,从火车站出站口搬到两百米外的汽车站里,挣了20元钱,下午帮人扛了一个口袋,挣了5元钱。他把5元钱攥在手里很久,在广场上又转了一圈,他的棒棒生涯就此结束。
他去药店买了一瓶止咳糖浆,他有些担忧,“这要回去了,又有点感冒”。他是个讲究的人,去车站对面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买了一双布鞋,15元,他说老板没卖他贵的,“我经常在这里买”。在重庆的最后一个晚上,唐永柏没睡踏实,但早上起来,还是穿得干干净净。他用多年来给别人挑东西的棒棒,挑着自己的两床棉被、一包衣服,慢慢地走过菜园坝火车站广场,他停下来喝了一杯豆浆,5角钱,他说回去就喝不成这个了。
车上,唐永柏一直看着窗外,他要再看看熟悉的重庆,当年毫无准备地来到重庆,然后一待就是15年。他跟朋友说过两三年还要来重庆看看,但又私下跟成都商报记者说,以后再也不来了。他把自己的棒棒放在了彭老板那里,说有人要就送给人家,他说“这个我就不带回去了”。
棒棒生涯
曾是生产队长,欠下债务外出当棒棒
唐永柏已经无法准确记得自己离开常郭村的日子了,他说15年了,几个村民也说“是有差不多15年了”。听说唐永柏回来了,左邻右舍的几个老人都来看看,“老了,背都弯了”。也有人调侃,“这么多年,混得怎么样嘛?”唐永柏声音低缓,又扬起脸说,“混得不好,但这么多年也没去要过饭,靠的都是力气挣钱。”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些年过来,他的确没有攒下钱,“年纪大了,几个钱都拿来吃饭吃药了”。他说外面的钱哪那么好挣,当棒棒靠的是力气,自己力气又已经不行了。
11月4日中午,回到常乐镇,他决定买点香烛纸钱给父母上个坟。
镇安办主任、常郭村支部书记赵荣兵陪同唐永柏回到村里,帮唐永柏搬行李。在唐永柏表示不愿去养老院后,赵荣兵安排他先跟其兄弟住几天,房子镇上、村上会想办法,特事特办,尽快进行修缮。
关于15年前为什么离开村子去当棒棒,唐永柏一度不愿提及。从他和村民口中,记者得知,10多年前,农村还要收农税等款项,因为按期收不上来,生产队长唐永柏以自己的名义向信用社贷款,找村民借的方式,把款交了上去。最后这些农村减负,这些款项都不需要再收取后,这些钱就更加收不上来了,而自己却背上了债务。11月4日,常郭村村主任温勉立也来迎接唐永柏。对于唐永柏欠款一事,他没有否定村民的说法。
练就火眼
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旅客需要棒棒
这么多年来,村里人少有唐永柏的音讯,只零碎听在重庆打工的村民回来说,唐永柏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帮人扛地毯。2004年,吴善耐夫妇在菜园坝小商品批发市场做地毯生意,门市临街,对面就是菜园坝汽车站、火车站,地毯销往周边各地,需要从门市搬到车站发货。吴善耐的门市刚开张的时候,唐永柏就在他的门市干活,没事的时候在这里歇脚,主要候着吴善耐和旁边门市的货物搬运工作。
唐永柏在这里干到2012年左右,地毯就搬不动了。一捆货就是一百斤左右,70岁的唐永柏力气大不如从前。搬不了地毯的唐永柏,就只有扛着棒棒到车站转悠,捡轻的帮人挑一下行李,从此成为了一个“野棒棒”。按行话,有固定雇主的棒棒,叫“家棒棒”,四处揽活的叫“野棒棒”。
当了棒棒15年,生意都是看运气。运气好的时候,一天有五六十元,运气不好的时候,就二三十元。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车站旅客哪些需要棒棒,也很清楚从北京、哈尔滨开过来的车,旅客的行李往往更多。
累了的时候,唐永柏常常在火车站一家本土连锁快餐店休息,这里可以随便坐,夏天还可以蹭空调。但他从来没在这里吃过饭,“一顿普通的就要二十几块”。
对于吃饭的花销,唐永柏每天计算得很准确,早上一杯豆浆、三个鹌鹑蛋、一个三角面包,三元钱,中午一顿5元,可以吃肉,晚上吃面5元。这些便宜的吃饭地点,都是他的固定选择。
菜园坝车站背后是一片山坡,轻轨和公路隧道穿过山体,立交桥盘旋在车站广场外。从繁华忙碌的街道往山上走,是清幽的小巷子,巷子里是错落的石梯,穿过巷子,半山坡有几栋老旧的砖瓦房,唐永柏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一个月90元,与三个人合租一个房间,房间里没有多余的空间落脚。
11月3日晚,周围住的几个背棒棒的老人来看望唐永柏,几个人挤在一起看电视,电视是一个17英寸的老电视,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又都为“唐老头”高兴,“回去以后享点清闲,不要再来了”。
大军消失:
时代变迁 棒棒是留不住的背影
很少有人比《最后的棒棒》导演何苦更了解棒棒这个群体,为了拍摄纪录片,他曾经当了一年的棒棒,成为重庆“最年轻的棒棒”。听说“最老的棒棒”唐永柏要回家了,何苦专程从渝北区赶到渝中区的菜园坝火车站,握着老人的手聊了很久。何苦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些年过来,他一直在关心棒棒这个群体,走在街头遇上了,他都会“跟踪”一段,棒棒越来越少了,在街头上并不那么容易遇上了。
重庆一度多达数十万棒棒从业者,每条街道上都有他们的身影。按照他的估算,目前重庆还在从业的棒棒人数1万人左右。“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慢慢变少的”,何苦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如果一个行业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消失了,那就真的说明这个社会已经不需要这个行业了。
△《最后的棒棒》导演何苦到菜园坝火车站看望唐永柏
何苦介绍,现在还在从业的棒棒,大部分都在五六十岁,他们中一部分是为了给儿女减轻负担挣点生活费,也过点自由的生活,真正像唐永柏这样靠这个职业谋生的并不多,所以,很多人觉得干不动了就回去了。而年轻人并不愿意再来当棒棒,他们进了工厂,去了工地。
何苦还发现,那些雇请棒棒的往往都是小门店,随着时代的发展,小门店也已经越来越少,有些转型去了大商场,有了自己的售后团队,有的转行去做更有效益的生意,还有一部分棒棒自己也转型做了生意,干了别的。所以,棒棒这个群体越来越少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何苦说,现代化的重庆离不开曾经数十万的棒棒的贡献,他们朴实、勤劳、真诚,给重庆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他自己在拍摄的过程中,也常常感动落泪,舍不得他们,但他们的背影又确实无法挽留。
成都商报客户端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原标题:重庆76岁“最老棒棒”退休:社会已经不需要这个行业了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