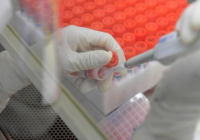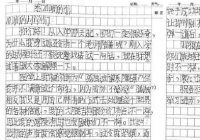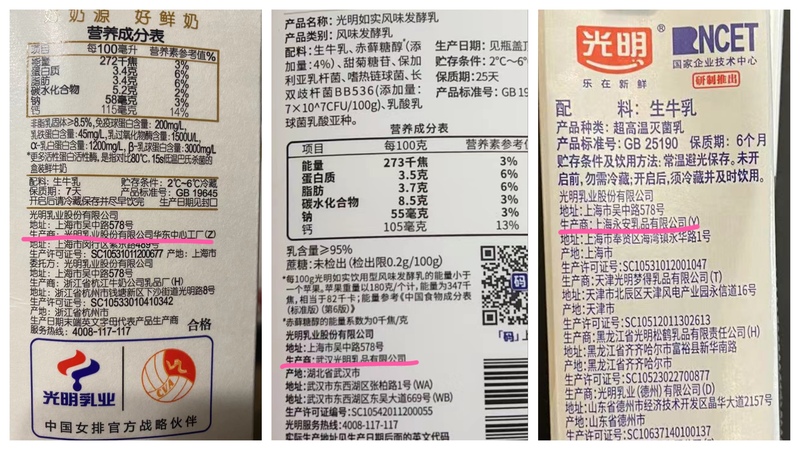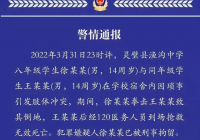爸爸是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期间的2020年3月4日深夜去世的。
两年多来,我时常梦见爸爸。梦醒时泪水还残留在眼角,脸庞贴着被泪水浸湿的枕巾,感到微微的冰凉……
爸爸患老年痴呆症在病床上躺了六七年,吃喝拉撒全靠专业护工照料。去世前的最后几年,他的器官各项功能衰减,靠呼吸机输氧、靠鼻饲进食、失语失聪、浑身不能动弹,长时间处于昏睡状态,只有偶尔吃力地睁开的双眼和体温能显示他的生命迹象……
就这样,爸爸熬过一年又一年。
2020年春节前,1月23日武汉因暴发新冠肺炎疫情而被“封城”。大年三十下午(2020年1月24日),我和妹妹陪妈妈到武汉长航总医院去看爸爸。在病床前,妈妈还竖起大拇指在他眼前晃动,为他加油鼓劲,希望爸爸能挺过这个疫情的寒冬。

在病床前,妈妈竖起大拇指为爸爸加油鼓劲,希望他能挺过那个疫情的寒冬。
随着武汉疫情的蔓延和“封城”气氛日益紧张,从2月初开始,医院要求所有住院的病人必须戴上口罩,爸爸戴上口罩后,虽然从外表上看好像没有异样,但可以想象,一个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90岁病人会是怎样一种感受。本来气若游丝的他既无力用手扯掉口罩,又不能用言语表达,本来就浸泡在苦难中奄奄一息的生命继续被折磨着……
我时常想象着爸爸在那个寒夜临终时的无言、无力、无助、无奈,“呼”天不灵、“叫”地不应的那种难以形容又不易被人觉察的痛苦……即使倾尽海水也难以描述他离世前内心的痛楚。
爸爸虽已走了两年,他的身影却时常在我眼前浮现,勾起我的锥心之痛和连连回忆。
我常常想,爸爸在世时如果我能对他有更多的理解、顺从和迁就,更加尊重他的意愿和生活习惯,或许现在我会少些遗憾和愧意,心绪也会更加安宁。
爸爸生前颇为节俭,那种极致的节俭令我无法认同,也因此我们之间发生过不少磕磕碰碰。
上世纪80年代末到2012年,爸爸、妈妈从湖北老家来到北京和我一起生活了20多年,在日常生活中,我曾无数次劝说爸爸不要过于节俭,但他依然默默地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旧习惯。
记得20多年前的一个春节,一家人在吃年夜饭。我给妈妈夹菜时不小心将一块粉蒸肉掉在地上,爸爸露出惋惜的神情并准备起身……我担心爸爸下一步会做出“不雅观”的事,便抢先起身弯腰眼疾手快地从地上捡起那快热呼呼的粉蒸肉,扔到厨房的垃圾筐里。
爸爸默默地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那顿年夜饭爸爸似乎吃得比平时要快,他吃完饭便放下碗筷去了厨房。不一会厨房里就传来水管的冲水声。我下意识地感到将要发生什么,马上从餐桌旁快步到厨房,只见爸爸把我刚才扔到垃圾筐里的那块肉捡起来用水冲洗后正往嘴里递……被我抓个“现行”。爸爸用尴尬和惊讶的眼神看着我,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大过年的,一块掉在地上的肉还这么在乎?我低沉而又大声地埋怨爸爸:“你这是干吗呀!”爸爸脸色凝重,继续嚼着那块粉蒸肉,双眉紧锁直视着我,像小孩做错事被大人发现后有些惶恐。
爸爸这种深入骨髓的节俭时时左右着他的行为方式,我们父子间磕磕碰碰的事也接二连三地发生。
爸爸喜欢看报纸,有时戴着老花镜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有关保健知识方面的文章他都一一剪下,自制成一本本“保健大全”。多年来我都会从办公室拿些看过的报纸回家给爸爸阅读。每天看过的报纸爸爸都会一份份地叠齐,十天半月的报纸就码成了一摞。爸爸“惜纸如金”,每次家里空出来的水果或牛奶外包装纸箱(盒),爸爸都非常细心地一个个拆开,然后一片片剪成A4纸大小,混夹进一摞报纸里。就连他和妈妈食用药品的外包装盒,他也舍不得扔掉,一片片地被捋得平平整整夹进看过的报纸堆,然后再用绳子捆成一摞一摞,整整齐齐地堆在房间,每月定期卖给收废品的,这是爸爸多年的习惯。那时一公斤报纸可以卖六七毛钱,爸爸卖一次报纸也就只有三五元收入。我多次劝爸爸,一斤报纸卖不了几毛钱,家里也不缺这几块钱,以后不要再卖了。爸爸总是默不作声,依旧我行我素。

看过的报纸爸爸都会一份份地叠齐,十天半月的报纸就码成了一摞。
记得一年春季的一个星期日,爸爸妈妈早早去逛公园去了。我起床后闲来无事,看到爸爸妈妈房间的一堆报纸已经捆好,摞得高高的,觉得有些“碍眼”,便心血来潮想处理掉。我知道小区里有一位河南老人负责的废品收购点,便自作主张地拎起几捆报纸下楼卖给了这位老人。那天中午爸爸回家,见房间的一大摞报纸没了,一脸阴沉地问我:“那几捆报纸呢?”我告诉他:“帮你卖了,卖的几块钱放在你床头柜上了。”
爸爸紧接着问:“你拿到什么地方卖的?”
“楼下那个收废品的老人呀!”
爸爸怒气冲冲地训我:“谁让你卖的?”我顿时感到诧异。
妈妈见状马上过来“打岔”:“这次卖了就卖了吧,以后报纸还是让你爸爸卖。”妈妈告诉我,爸爸积攒的报纸总是舍近求远地跑到小区外马路边上一个废品收购点去卖,因为那里的收购价要比小区里每斤多一毛钱。
“你爸爸节省惯了,老毛病是改不掉的,你以后少管他的闲事。”妈妈宽慰我。
那时我“年轻气盛”,理解不了爸爸的内心世界,以为爸爸过于节俭的习惯是因当年家庭条件不宽裕,为抚养我们兄妹四人而养成的。现在子女们早已长大成人,家里经济条件也大为改善,爸爸应该与时俱进地改掉过于节俭的习惯。于是,在日常生活中,我总是试图影响和改造爸爸的习惯和观念,想让爸爸晚年的生活过得舒适潇洒些,不再为钱而愁。但未料到这样的“好心”实则一次次在无意中伤害了爸爸的自尊和感情。
我现在才明白,对父母的爱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尊重、顺从、迁就、包容那个时代赋予他们的在我们今天看来过时的生活方式和观念。
在爸爸晚年病重住院这一段时间里,我曾经幼稚地幻想,万一爸爸哪天走了,我们子女一定要给节俭一辈子的爸爸办一个体面的告别仪式,让节俭一辈子的爸爸第一次也是最后“风光”一把。
爸爸的后事家人虽早有心理准备,但他在武汉疫情“封城”期间突然去世,还是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使得预想的计划成为泡影。在“封城”时期严格的管制下,我只能匆匆从医院太平间值班工人那里给爸爸买了一套普通寿服,裹身入殓。按武汉防疫指挥部的统一规定,武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第二天一早就来医院太平间拉走了爸爸……没有告别仪式,家属也不能随灵车一起送亲人最后一程,一切都简化得不能再简化,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也许这正暗合了爸爸一辈子节俭的秉性。
万幸的是,在2020年那个特别的清明节十天前,我接到了殡仪馆通知领骨灰盒的电话。第二天大清早我就匆匆赶到武汉殡仪馆,领到了爸爸的骨灰盒。为让爸爸早一点入土为安,我抱着骨灰盒又驱车百里之外的老家蔡甸玉笋山墓地和家人们一起安葬爸爸。

一块带了多年的手表陪爸爸骨灰盒放入墓穴。
初春的玉笋山,山风吹拂着脆绿的松叶,悉悉索索,凉意阵阵。当孤零零、沉甸甸的骨灰盒将要被安放进墓穴时,我缓缓地摘下了自己手上戴了多年还带着身体余温的手表,随着用黄绸缎包裹的骨灰盒一起放入了墓穴。那块手表是我几年前出访瑞士时花五六百美元买的,它也是爸爸这辈子“享受”到的最奢侈的一件物品,而且是在身后。
两年了,我还为此不安,担心哪天梦见爸爸时,他会怒气冲冲地训我:“你这个败家子。”
(2022年清明节前夕)
文/夏春平
原标题:爸爸的节俭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