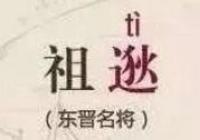“在场为人父母的,有多少人认为,现如今孩子可以完全不学习编程?”

面对嘉宾突如其来的提问,全场上百位与会者,只有一位父亲“勇敢”地举起了手。这位父亲还被调侃道:“未来您家孩子可能会成为一名经理人。”
这个颇有意味的一幕发生在卡达尔举行的2017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上,峰会两年举办一次,其间发布被称为“教育界诺贝尔奖”的WISE教育奖,以及有关教育创新的最新方法和案例。今年,来自全球的“取经者”纷纷将目光聚焦到了人工智能。
或是多次人机围棋大战以来,机器一路胜出的缘故,“人工智能”似乎成了当下只要开大会就必谈及的词语。而人类中最在意灵魂和精神建设的群体——教育工作者,对于这个新技术逼近的现实,更是显得有些焦虑,摩拳擦掌、绞尽脑汁准备应对之策——
人工智能究竟会对教育造成多大的颠覆,教师是否会被人工智能替代,孩子的个性化教育能否借人工智能之势实现,而对于农村落后地区,新技术带去的是更大的数字鸿沟还是逆袭机遇……
新技术对教育的颠覆远超科幻小说的想象?
国际科幻界最高奖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也受邀来参加这次峰会,不过她更多是以童行计划发起人的身份来和与会者交流。后者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公益型教育计划,之所以说是面向未来,就在于郝景芳希望在计划中注入更多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元素。
在自己的科幻作品里,郝景芳时常写人工智能与人类对抗故事,“通常情况下,人工智能一上来就不怀好意,磨刀霍霍,分分钟准备取代人类,成为地球的主宰者,那是小说需要冲突感,对抗感”。
而面对现实世界,郝景芳的选择是相信技术,依赖技术。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我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前景的预判,远比自己在小说里所体现的态度乐观得多!”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个性化教育上。
郝景芳说,人工智能未来完全有能力“协助”甚至“取代”教育工作者的部分工作。基于认知体系,人工智能可以给孩子以“千人千面”的教育内容。
她举了一个场景的例子:一个“吃”了很多优秀教案、教研产品、学生培养规律数据的人工智能,在最初和孩子“接触”时,就埋下一个个性化评测的伏笔,摸清楚孩子在某个领域的知识水平,“对话”结束后即可拿出一份智能推送,给孩子以及孩子家长一个判断的依据——哪些知识已经掌握,哪些还需要学。当然,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还可以有教学可视化等手段。
可以设想用人工智能来教授知识。不过,这个过程,绝不是简单地把一个饱含丰富知识的芯片直接插入人脑的过程;其应用场景,也并不等同于每个孩子“手里捧个智能手机”那么简单。其重点是,让老师或家长了解每个学生的情况,并且找到适合不同学生的学习内容。
在峰会上与郝景芳对话时,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约格·德莱格提出一个观点,即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学习,其真正的核心,是给老师省下时间去关注“真正重要的东西”——老师除了要“教知识”,更需要“教孩子”。
这一点,“互联网教育独角兽”沪江创始人兼CEO伏彩瑞也颇有感触,他在峰会上就提出,人工智能只是把教学过程中那些长期以来被视为“负担的东西”“那些不必要的大部头”彻底解放掉,总结下来就是“效率”两个字。
省下的时间做什么?和孩子交流,让学生认知自我、更好地发展自我。关于爱、感情,这些才是人类能守住的东西。
看看当下的课堂,有时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教师可能需要把80%的时间花在传递标准化知识上,而只有20%的时间,真正用在关注孩子。伏彩瑞说,时间分配颠倒过来,似乎更为合理。毕竟,“教育的本质不是简单的知识传递”。
教授人类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 人工智能行吗?
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未来真人教师是否会被人工智能全部替代?这也是峰会上,与会者讨论最多的问题。
约格·德莱格认为,有了之前的讨论,真人教师依然会是未来课堂的中心,“我们是使用技术这个工具给老师赋力,而不是夺走他们的权利”。
事实上,还有很多东西是人工智能所教不了的。作为此次峰会最受瞩目的大奖——WISE教育奖最终授予了加纳阿社思大学创始人帕特里克·奥瓦,由他所创立和管理的阿社思大学作为一所私立的非营利教育机构,在短短十几年间就成了加纳首屈一指的大学。
这个奖项的背后有一个令人震撼的故事。1985年,帕特里克·奥瓦带着口袋里的50美元和美国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全额奖学金离开加纳,前往美国。在接下来的4年里,帕特里克·奥瓦通过斯沃斯莫尔学院的人文科学教育感受到了“批判性思维”的力量——这与他之前在非洲所接受的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毕业后,帕特里克·奥瓦加入微软公司,并成功地设计了拨号连接互联网的方案。但帕特里克·奥瓦还是决定回到加纳,计划成立一家软件公司。但是,他四顾茫然:不仅没有合适的技术性人才,也没有符合道德领导力的人才。
帕特里克·奥瓦返回学校,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如何创办一所能培养人的领导力和正直品格的大学。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帕特里克·奥瓦说:“我决定在加纳创建一所新的大学,不是因为加纳缺少大学,而是因为这里缺少能教授21世纪所需技能的大学。加纳的现有大学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忽略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忽视道德伦理或协作精神。”
而道德、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等这些人类所引以为傲的品质,似乎都是人工智能没法教授的。它们自己“学会”,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如今,这所俯瞰着加纳首都阿克拉市的大学已经扩展到了607亩,并拥有近900名学生。值得一提的是,阿社思大学还于2008年建立了一套学生荣誉守则体系,要求学生保证他们的行为将符合道德水准——这在非洲大学中还是首例。
新技术带给农村是更大的数字鸿沟还是机遇
对于农村落后地区,新技术能否带来教育上的逆袭机遇,成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眼下的最大期待。
郝景芳对此比较乐观,她说,新技术本身的出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填补“数字鸿沟”。她到农村支教发现,孩子们一双双大眼睛盯着村里的老师:“老师,为啥太阳那么亮?”
要求村里的老师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并深入浅出地讲一些天体物理的知识,在郝景芳看来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这些老师也没能回答上来。而郝景芳带去的新媒体课件,则让孩子们清楚了“前因后果”。
“这就是新技术的力量,尽管这只是很低级的形式,但面对偌大的农村需求,依然显得非常匮乏。”她说。
当然,这需要一个前提,即要有人把这些最新技术成果“搬”到农村,让农村落后地区的孩子真正享受到技术的红利,不然“数字鸿沟”还是会越来越大。
在接受采访时,郝景芳反复提到一个案例,即“互+”计划——一边连接成千上万的乡村学校,而另一边则是各个城市甚至全球的教育名师,他们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足不出户,通过一个互联网软件平台给那些山区的孩子上课,带去音乐、美术、科学、外教口语等课程资源。
在过去两年,这个互联网计划已经连接了13个省3000多所中学,有将近100多万的乡村学生受益。而这个计划的发起者就是伏彩瑞。
伏彩瑞也因此成为此次峰会创新项目唯一来自中国的评委。峰会上,他还受邀向与会者分享他在教育公平、促进农村教育方面的实践。
演讲结束后,峰会现场来自西班牙、加纳、刚果等国的嘉宾纷纷找到伏彩瑞,向他表达合作意向,期待“互+模式”能够输出海外。
事实上,不管是支教,还是直播技术都早已不新鲜,但“互+”计划却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而这,在郝景芳看来就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一种“落地”。
正如约格·德莱格所说,教育问题的关键似乎从来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技术如何使用,以及其背后的资源如何分配。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