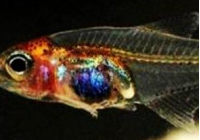澎湃新闻消息,12月8日起,世界首部全手绘油画电影《至爱梵高》在中国公映,通过大银幕上流动的梵高油画笔触,可以让观众一览这位后印象派绘画大师的风采。随着电影的放映,梵高又成为公众讨论的对象。120多年前,梵高不会想到他的画作会如此受到欢迎,公众也那么热衷于了解他的一切。
关于梵高的死亡,一个流传已久的版本是死于自杀。而随着美国两位艺术史专家史蒂文·奈菲(Steven Naifeh)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Gregory White Smith)创作的《梵高传》出版,人们开始接受另一个梵高之死的版本——死于误杀。这一权威版本的《梵高传》中文版之前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本文选摘于《梵高传》。

出人意料的是,人们对导致文森特·梵高在37岁就英年早逝的这一影响如此深远且后果可怕的意外事件所知甚少。
总的说来,可以肯定的是他死于1890年7月27日在巴黎以北20英里外的奥威尔镇或是附近所受的枪伤。他是在所居住的旅店吃完午饭后,带着绘画工具外出去画画的某个时间受的伤。在晚饭刚过的时候,他回到了拉乌旅店,上腹部中弹。他请了医生来治疗,但他的伤口却是致命的。大约在30个小时之后,文森特离开了人世。
当时照顾他的两个医生检查了伤口,并动手仔细探查了他的上腹部。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首先,子弹并没有穿过身体而是停留在脊柱附近;第二,造成伤口的枪是一把小口径的手枪;第三,子弹从一个罕见的倾斜角度射入体内(不是一直向前的);第四,枪是从距离身体较远的地方开的,而不是从很近的地方开的。
关于枪击没有任何物证。没有发现任何枪支。文森特在离开拉乌旅店时所带的那些绘画工具——画架、画布、颜料、画笔、素描本——一件都没有被找到。枪击发生的地点从来没有被最终确认过。没有进行过尸检,那颗致命的子弹没有被取出来。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枪击的目击证人。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站出来确证文森特在枪击发生期间(大约五个小时)的行踪。
在文森特返回拉乌旅店之后的数小时内,关于他是如何受此重伤的各种流言开始满天飞。这些流言迅速地整合成为一个故事,描述了在7月27日所发生的状况。根据这个故事(被几乎所有后来的记述所采用),文森特从他所住的旅店的老板古斯塔夫·拉乌那里借了一把左轮手枪,并在那天下午他通常外出作画的时候带上了这把手枪。随后,他爬上了河岸,步行了一段路程之后,来到了位于镇外上方的那片麦田。就在这片麦田里,他放下他所带的画具,开枪自杀。这一枪未能致死(子弹没有射中心脏),但却使他失去了意识。等到他重新苏醒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所以他无法找到那把枪。他只好从陡峭的河岸上蹒跚而下,回到拉乌旅店去寻求医疗救护。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故事。它给一段不可否认的悲剧人生加上了一个合适的悲剧性结尾:一位痛苦而不被赏识的艺术家为了逃避世人的漠视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不仅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很快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在梵高死后的数十年中,他很快声名鹊起,享誉四方,这个故事当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了1934 年,这个故事已经被欧文·斯通永远地写进了他的畅销小说《渴望生活》,文森特在麦田里自杀的故事永久地成为这位艺术家传奇人生的一部分。20年后,在上世纪50年代,文森特·梵高的声誉又上升到了新的高度,1953 年是他诞辰100周年纪念,三年后由《渴望生活》改编而成的奥斯卡获奖影片上映后,他的传奇声誉成为了永远的神话。
然而,当我们回顾已有的证据时,我们会发现可以证明这个故事的可信和可以被证实的证据几乎没有。这一附录的目的,就是给出一段更为符合7月27日事件的已知情况和当事人的记载,仔细找出传统叙述版本的来源,并且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看来那个记述远不够可信。

在电影《渴望生活》上映的同一年——1956年,一位名叫雷内·萨克里顿的82岁的法国人站了出来,他讲述了关于1890年他在奥威尔所认识的一个奇怪的画家的故事。雷内是一位富有的药剂师的儿子,他在巴黎郊区长大,梵高去世的时候他16岁。他在巴黎最著名的公德赛中学上学,保罗·魏尔伦和马塞尔·普鲁斯特也曾在这所中学学习,斯蒂芬·马拉美和让-保罗·萨特曾在这所中学任教。
据雷内所说,这把枪是古斯塔夫·拉乌卖给(借给)他的。古斯塔夫·拉乌是旅店老板。
在镇上的时候,雷内和他的追随者有另外一种他们喜欢的消磨时光的活动:捉弄加斯顿的朋友,就是那个奇怪的、叫文森特的荷兰人。他们把盐放在他的咖啡里,然后在远处看着他把咖啡吐出来再生气地咒骂。雷内回忆说他们把一条蛇放在他的颜料盒里,当他发现这条蛇的时候,他几乎要晕了过去。雷内注意到文森特有时在思考的时候会吮吸干的画笔,所以在文森特没看到的时候,雷内就用红辣椒擦拭画笔。雷内承认这些行为都是为了“使文森特发狂”。
文森特面对这些捉弄选择了不生气。逐步升级的捉弄也没有让雷内成为他的敌人。文森特给这个16 岁的少年起了一个绰号“恐怖的熏鲱”, 以玩笑的方式赞扬雷内是个天生的捕鱼者。文森特经常看到他穿着那套狂野的西部行头,所以也叫他“水牛比尔”。但据雷内所说,因为文森特有很“奇怪的口音”,所以他说出的名字是“衰牛屁尔”,每次他说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会引起人们的嘲笑。
虽然文森特避免和跟着雷内的那伙人接触(就像在任何他居住过的地方,他都避免和让他烦恼的人接触一样),但他承受着雷内的戏弄却从不抱怨,甚至脾气很好(他在写给提奥的信中从没提过被戏弄)。这两个人继续在拉乌旅店里喝酒,也在古老的瓦兹河畔的偷猎人酒吧里喝酒,这个酒吧距离小镇有一英里远——雷内称这里是“我们最喜欢的酒吧”。文森特原谅喜欢恶作剧的雷内,部分是因为他想与加斯顿保持少见的良好友情,据雷内所说,文森特认为加斯顿在绘画方面的想法是超前的。当然他也很感激这对兄弟经常为他支付酒吧的账单。萨克里顿兄弟对他而言也是极好的陪伴——他们来自一个极受尊重的资产阶级家庭,在文森特吸引提奥和他的家人到奥威尔来的虚妄计划中,这对兄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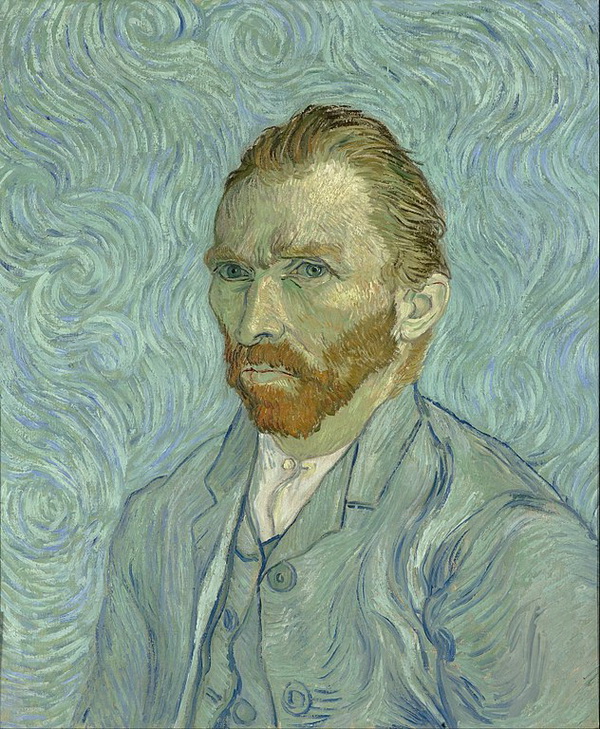
在梵高百年诞辰纪念后的第十年,另一个目击者站了出来。这位女士的父亲1878年曾住在梵高在奥威尔最喜爱的作画地点附近,那儿也是伟大的法国巴比松画派名家查尔斯·多比尼过去的住所和花园。20世纪60年代,当她接受梵高的传记作者马克·特拉包特的专访时,只用了她婚后的名字,利贝热夫人。1890年时她快有20岁了。
利贝热夫人并不接受梵高在奥威尔公墓上的麦田里受了致命伤这一传统说法。她告诉特拉包特: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不说出真相。并不是在那里,什么公墓旁边……梵高离开拉乌旅店,去往夏彭瓦尔村。在布歇街他走进了一个小农场。在那儿他躲在了粪堆后面。然后他做出了几小时后导致死亡的行为。
利贝热夫人说她的父亲是个杰出的公民,很多年前他就告诉了她这些。“这都是我父亲的亲口所言,”她说,“为什么他会想要编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来伪造历史呢?任何认识我父亲的人都会告诉你他从来都是让人信任的。”
数年后,另一个奥威尔居民,贝斯夫人证实了利贝热夫人的故事。她告诉一个记者说她祖父“那天看见文森特离开拉馆旅店去往夏彭瓦尔村”。这位目击者说,她祖父看见梵高走进了布歇街的一个小农场,然后听到一声枪响。贝斯夫人说等过了一会儿,“他又自己走进了那个农场,但那儿看不见其他任何人。没有手枪也没有血,只有一堆粪”。
夏彭瓦尔村和公墓后的那片麦田处于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者在拉乌旅店的西边,而后者在它的东边。贝斯夫人提到的布歇街和通向夏彭瓦尔村的路相交,就在拉乌旅店西边不到半英里外的地方。当时,通向夏彭瓦尔的路(现在叫卡诺街) 两旁是带着围墙的农场,正和两种说法里描述的一样,而这两种说法时隔近30 年。粪堆是这种农场的一个普遍特征。文森特经常沿着通往夏彭瓦尔的路步行去往四英里外的蓬图瓦兹,在那儿他能享受到更好的火车邮递服务, 收取巴黎寄来的物资或者寄送他自己的作品。通往夏彭瓦尔的路还直接通向瓦兹河的一个河湾,此处位于奥威尔和蓬图瓦兹中间,在那儿经常能找到雷内·萨克里顿,一来那里是垂钓的好地方,二来那儿有他最爱的酒吧。雷内总以这儿为起点开始他的冒险旅途,沿着通往夏彭瓦尔的路进入奥威尔镇。
夺去文森特·梵高性命的那次枪击可能并不是发生在麦田,而是在通往夏彭瓦尔的路上的某个农场的里面或附近,就像利贝热夫人和贝斯夫人所叙述的那样。另外,射出致命子弹的那把枪或许并不是文森特·梵高带进农场的,他对枪支一无所知也根本不需要它,带进那把枪的也许就是去哪儿都带着380口径小手枪的雷内·萨克里顿。他俩可能是在通往夏彭瓦尔的路上偶遇对方的,或者是一起从他们最爱的酒吧回来。几乎确定无疑的是加斯顿和他俩在一起,因为文森特会尽可能地回避雷内,不论是当雷内独自一人还是和他那帮小跟班们在一起时。
一直以来雷内都刻意地激起文森特的怒火来戏弄他。文森特也有过暴力发泄的历史,尤其是在酒精的刺激下。一旦雷内帆布包里的枪被掏了出来——无论是蓄意还是意外,在任性妄为、对西部荒原充满幻想的少年,对枪支一无所知的酒醉画家,和一把年久失修、随时可能走火的老枪之间,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在受伤的状况下,文森特一定是扔下了所有随身携带的画具,踉踉跄跄地冲上街道,向拉乌旅店走去。起先,他可能不清楚自己伤得有多重。伤口没有大量出血。但最初的冲击一过,腹部伤处传来的疼痛一定令他极其痛苦。萨克里顿兄弟很可能是被吓坏了。他们是否试图救助文森特也不得而知,但显然在匆忙冲入无尽暮色中之前,他们还有时间且足够镇定地收走了那把手枪以及文森特的所有随身物品——这样,当贝斯夫人的祖父紧接着去查看(如果他确实做了)的时候,就只发现空空的农场和粪堆了。

梵高的讣告
对1890年7月27日系列事件的这个假设性重构解开了许多矛盾,也填补了很多缺口,并将自枪击发生那天起就主导着梵高神话的传统自杀说法中杂乱的碎片拼凑在了一起。
它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有一名警察第二天就着手调查此事,发生地附近的所有证据仍消失得如此之快而且再不见踪影。以当时的伤势,文森特根本无法事后清理得如此干净,除了有罪的共犯,没人有理由将他遗留下的不值几个钱的大部分画具拿走、藏起来或是处理掉。萨克里顿兄弟在暮色中匆匆掩盖此事时,或许也漏掉了些什么——一滴血或者一个废弹壳,但警察永远也不会找到,因为他们其时正在搜查的是远处的麦田,而不是通往夏彭瓦尔的路上的那些农场。
它解释了检查文森特伤口的医生在报告中提到的奇怪之处:首先,枪击是在腹部而不是在头部;其次,子弹是以一种不一般的倾斜角度射出的——而自杀时子弹通常是直射进去;再者,子弹显然是从距离文森特“很远的”地方射出的,远到他根本不可能扣动扳机。
它解释了文森特是怎样在负伤的情况下从枪击现场到达拉乌旅店的,尽管腹部中弹,每走一步疼痛就更为剧烈。即使是从布歇街到旅店这样一段相对较短的半英里路程——一段平缓道路上的直线路程——也必定让人耗尽了力气。在逐渐昏暗的暮色下,顺着一条陡峭崎岖的小路,沿着森林密布的河岸从那片麦田走下来(后来的传说是如此描述的),在他当时的状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它解释了分别有两个目击者在事件发生当晚看到文森特走在通往夏彭瓦尔的路上。据目前所知,没有目击者看见文森特出现在传统说法中的开枪自杀的麦田(在小镇的另一头)附近。也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出现在从麦田到拉乌旅店必经的长路的任何一处。因为在7月的温夏夜,许多村民在日落后出来吃饭喝酒、抽烟聊天(拉乌一家也是如此)。文森特可能走的所有从麦田到拉乌旅店的道路都是热闹的公共街道,并且他那样明显地步履蹒跚,总会有人在那晚看到他经过那条传说中的路。
它解释了为什么文森特自杀后没有留下遗书,也解释了为什么提奥在枪击发生后的数天内整理文森特的房间和画室时并没有发现任何“道别”的痕迹。它解释了为什么那天文森特在远足时还费劲地拿着一堆画布、颜料和其他必需品——如果他根本不打算回来的话,他不太可能这么做。
它解释了为什么当他第一次(而且是唯一一次)枪击失误后,没有“彻底解决自己”,反而选择了一条小路,痛苦而尴尬地回到他在拉乌旅店的阁楼小屋中。
它解释了关于梵高的自杀叙述中提及的一垛干草堆的神秘消失。最初一则有关枪击的书面记录(在一个参加葬礼的追悼者的信中)说文森特“在开枪自杀前将他的画架靠在了一垛干草堆上”。但是后来对故事的复述中就省略了这一细节,大概是因为在许多人误认作梵高最后的画作《有乌鸦的麦田》中,没有干草堆出现。实际上,经后来的目击者回忆,最早报道中的“干草堆”几乎可以肯定是“粪堆”。
它解释了为什么带来致命一击的枪的来源在70年后才被揭露,即使在枪击发生时应该有不少人认识这把枪。奥威尔是一座小镇,在法国乡间左轮手枪还是件稀奇物,古斯塔夫·拉乌的生活十分公开,而雷内·萨克里顿又喜欢带着枪到处公开炫耀,所以两人的许多朋友肯定对这位旅店店主的罕见武器十分熟悉。拉乌的女儿艾德琳在其早先关于梵高之死的叙述中没有提及任何她父亲和致命武器之间的关系。直到20世纪60年代她最终承认父亲拥有武器时,她却将雷内·萨克里顿从她的叙述中省略掉,声称文森特是为了驱散乌鸦才向她父亲提出请求,并直接从她父亲手中拿到枪的——显然这是一个经过改编的说辞(很可能是她父亲的意思),目的是向警方解释他的手枪是如何被卷入了这场致命的枪击案中,也掩饰了他自己将枪交给一个臭名昭著的好斗少年的过失,同时让萨克里顿兄弟(他们的父亲是富有和显赫的主顾)免于接受令人尴尬的漫长调查——甚至是审讯。这一切都基于拉乌几乎肯定地认为这是一个不幸的意外,或充其量只是一个不幸导致了严重后果的青少年的恶作剧。
最后,这个重构解释了为什么根据当时的目击者的说法,文森特对自杀行为的“忏悔”是那么犹豫,言不由衷,以及躲躲闪闪。当警方直接询问文森特说:“你是不是想要自杀?”时,他不太确定地回答说:“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当他们告诉他企图自杀是一种罪行时,他似乎更关心其他人会不会被问责,而不是他自己是否会被定罪。“不要指控任何人。” 他回答说,“是我自己想要自杀的。”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推论,任何自杀都本应包含个人的动机和单独的行动,既然如此,为什么文森特还要竭力地主动声称这件事是他独自一人所为?为什么他力劝警官不要因枪击“指控任何人”,并坚持独自承担所有责任?文森特早前辩解说没有其他人参与此事,令人颇为费解,这种辩解表明了一个意图——实际上,是一种决心,他想保护萨克里顿兄弟,不让他们和此次事件有任何牵连。

梵高和兄弟提奥之墓
但是为什么文森特会如此大费周章地保护萨克里顿兄弟,尤其是折磨他的雷内,使他们免于警方的调查甚至是起诉呢?为什么明明他是一场可怕事故或更糟糕状况的受害者,却还反复“坦白”说是自己想自杀才开了枪?
我们相信答案是因为文森特渴望死亡。“可怜的家伙,他没有享过多少福。”提奥在文森特临死之际的床边如是写信给他的妻子,“要是我们能让他更相信生命的意义就好了。”来奥威尔参加葬礼的爱弥尔·贝尔纳描述说文森特曾表达了“求死的欲望”。另一名文森特临终之际的见证者保罗·加歇医生仅仅在葬礼两周后就写信给提奥,表达了对“文森特对于生命的不折不扣的蔑视”的敬慕,并将文森特的结局与拥抱死神的殉道者相比较。正如文森特自己曾写过的(且在下面加了醒目的下划线)“我: 不会特意寻死,不过一旦死亡降临,我也不会逃避”。
实际上,不论是意外、疏忽,还是恶意所为,雷内·萨克里顿可能带给了文森特一种他期待已久却不愿或不能自己实施的解脱,因为文森特终其一生都将自杀贬作“道德上的懦夫行为”和“不诚实的人的行为”。在结束了糟糕透顶的巴黎探访之后,文森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给提奥和他的小家庭施加了多重的负担,毫无疑问他觉得自己 “抽身离开”的机会到了——正如他1888年从巴黎离开一样,再不让弟弟继续为他头痛。
达到了这些目的,文森特再将萨克里顿兄弟——即便是淘气、粗心的雷内——拉进来接受公众质问和忍受羞辱就没有必要了。
原标题:至爱梵高,但他其实死于一次恶作剧式的误杀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