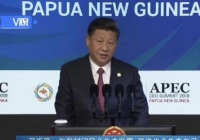双雪涛过去并不相信自己有写小说的才能。
人物微信公众号消息,他以为一生也就这样度过了,在银行里整理材料,偶尔出门跟客户吹吹牛逼,闲的发慌的时候,用1000本电子书抵抗人到中年的虚无。
直到他真正下定决心动笔写作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翅鬼》,在那21天里,他过着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的双重生活。那个翅鬼在晚上张开翅膀,飞往雪国,策划着一场蓄谋已久的逃亡。
《翅鬼》一举夺得大奖,双雪涛不顾众人劝阻从银行裸辞,「我想吃写作这碗饭,赴汤蹈火,写出牛逼的小说。」他说。
写作课——《像小说家一样写作》,是他首次公开地、系统地、完整地讲授自己的创作方法与经历。他希望在课程里告诉初学者们如何从生活的泥沼中挣脱出来,用自由的内心和自如的技巧去写作,才能真正走进小说的平行时空。
「怎么得到自由。」他在微信里打出了这句话,「就是我要讲的。」
打开门
双雪涛先生从未想过北京会以这样的方式迎接他。2015年9月4日下午,他乘坐G220次高铁从沈阳北站出发,3小时58分后抵达北京南站。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放下行李,他和前来接风的文学圈朋友们一同驱车去吃火锅。不料天降大雨,在这个周五的晚高峰,整座城市「像一个烂泥塘一样」,半小时才艰难地往前挪动了一公里。他在心里暗骂:「一到北京就是下马威啊。」
时年32岁的双雪涛是来北京报到入学的,他是人大文学院首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俗称「作家班」)的学员。一年前双雪涛凭在《收获》上发表的《跛人》刚获得了些许名气。27岁之前,他的生活与写作几乎毫无关联,他是沈阳一个庸碌的银行职员,每天与数量庞大的钞票打交道,做嵌入行政体系中的一颗螺丝钉,严格执行领导的想法,「领导说:弄!我们就弄。」
相比而言,作家班同学来头都不小,有人得过鲁迅文学奖,有人小说销量破百万,导师们更是成名已久,阎连科、刘震云、梁鸿都来了。来到北京的缘起是一次偶然,一位前辈作家翻《收获》,看到了最末的那篇《跛人》。这个陌生名字的作品冲击力太大了,她问《收获》编辑要了双雪涛的电话,直接打了过去:「你要不要来作家班?」
双雪涛毫不犹豫地决定就此换一个环境:「我那会儿在沈阳就是生活很平静,天天工作……(但)我到了一个我有点要窒息,就是那种平静和那种安全已经到了让人不太舒服的时候了。」沈阳是湖泊,但北京是河流——前银行职员双雪涛被召唤来了北京。
他念旧,此后只要回到沈阳,总要找来关系好的前同事小聚。这时,他会想起在银行的日子。「档案放在哪里」、「新做的表格在哪个文件夹」、「银监局马上就到,赶紧整理一下材料,不要给领导打脸」的咒语在那5年间箍紧了他的生活。那时他二十来岁,能喝小一斤白酒,跟客户吹起牛逼也从不觉得可耻,最爱听每月工资到账响起《加州旅馆》的短信音乐——「We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但是他在其中始终是异类,并最终成了单位里第一个裸辞者。
和双雪涛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一个晴朗的秋日午后,他蓄了须,戴黑框眼镜,一身运动装,打算采访完去踢球。在新的城市,他不再因为写作而有点特殊、被大家迁就,相反,他身边聚集了很多为艺术而活的创作者。聊到对北京的印象时,他眨巴着眼睛想了会儿,指了指窗外西斜的阳光:「每当这种阳光明媚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北京。」爱来得轻巧,厌恶也就在一瞬之间:「每当雾霾的时候,我觉得北京是我能够想到的最坏的城市。」
双雪涛迷恋北京的这种两面性,这是任何一个东北城市都不具备的。北京有一种乱糟糟的活力,「像一只大怪兽一样往前冲」。东北则直率,明快,刀下必须见血。他在北京生活两年,母亲、妻子和4岁的儿子都还住在沈阳。每隔半个月,双雪涛会回家一次。
新书《飞行家》几乎都是在北京写的,双雪涛的笔下第一次出现了移居北京的东北小年轻。有困惑,有分裂,有矛盾。
写作、喝酒、踢球、看电影,在北京,双雪涛心甘情愿过上了「就这几样事来回做」的乏味生活。当然,也是为了向他的文学偶像、信奉「写作是一种职业」的村上春树看齐。他住在人大家属楼的双人间,床和书桌紧挨在一块。每天9点起床,天光大亮时坐到书桌前,泡好茶水,手机调成静音,等待还处于朦胧梦境的脑袋缓缓苏醒。烟灰缸和打火机是必备的,要放在不用转头就能摸到的地方。
写小说是双雪涛人生中最具耐心的时刻,理想状态是「努力地吸一口气,一口气写下来」。但灵感并不会总是眷顾他,解决方式只能是来回折腾式的缠斗,卡壳了就把音响拧开,在《三套车》或《野子》的悠长曲调间静静吸上一支烟,歇一会再起来继续死磕。一天下来,平均水平是800到1000字,也有颗粒无收的时候,「有时候5个字都很正常」。
职业作家像小卖店老板,你每天早上要做的事是把门打开,有可能客人络绎不绝,也有可能一个客人也没有——他认可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这个比喻。总之,你只有打开门,坐在那里,客人才有可能来。
李子长在地里
9月中旬,双雪涛在北京一家书店开《飞行家》的分享会,对谈嘉宾是张悦然、编剧史航和《绣春刀》的导演路阳。现场的近两百个位子早不够坐了,站着的人群一直蜿蜒到场子外层叠的书架之间。对谈结束后,一个胖胖的年轻人奋力挤开人群,揣着三本书去问「涛哥」要签名。他说自己是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学生,仰慕双雪涛许久,斗胆要个微信。双雪涛爽快地答应了,这个中戏学生拍手叫好,喊着「喝酒撸串带上我」。
2016年,几乎大半个文学圈都在谈论这个横空出世的文坛新秀——尽管他已经不再年轻了。这一年,双雪涛陆续出了三本书,除了《平原上的摩西》外,《聋哑时代》、《天吾手记》都是积压了4年的旧作。奖项也纷至沓来:华语青年作家奖、中国新锐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小说佳作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迟来的大师」这句夸赞被印在了《平原上的摩西》的腰封上。
小说家赵志明评价双雪涛「天性幽默,敢于自嘲,一件寻常的事情由他说来便也舌灿莲花」。他第一次见到双雪涛是在北京,一位诗人组织的家宴上。羊排佐以白酒的两三个小时里,这个瘦高的东北小伙掌控了全场,「在一群惰性元素中,雪涛作为一个活泼元素,是当仁不让的酒司令,容易激发大家开怀畅饮。」
双雪涛说自己就是个普通人,因此顺理成章地「和生活打成一片」。《平原上的摩西》的电影改编权交到了青年导演张骥手里,过程异常顺利。事前张骥还有些发怵,因为听说「他这个小说前面好像去过一些公司」。两人在微信上聊了几句、喝了一顿酒后,觉得投缘,第二天酒还没醒,就晕晕乎乎地拟了份合同,一人按个手印,这事就算应了下来。此后两人成了常去吃涮肉的朋友。
一位作家朋友观察到这位同龄人旺盛的喷薄的创造力,就像是排量3.0的汽车引擎,「一个汽车装了3.0,它肯定用一辈子都是3.0的。」他从藏污纳垢的现实中来,这一点恰恰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养分。
仅从成长轨迹上来看,双雪涛和大多数工薪家庭的子弟没什么两样。从吉林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选择了「父母那一辈眼里头旱涝保收的最优解」,按部就班地进入沈阳一家政策性银行工作。栾绍华和双雪涛同年进入银行,在栾绍华的印象里,直到2012年辞职前,双雪涛一直都是单位的文艺骨干。「创作剧本啊,带着大家排练啊」,他总能迅速读懂交流对象的特点,让人相处起来特别舒服。
栾绍华反复向《人物》记者强调,双雪涛「是在体制内会做得很好的一个人」。辞职「并不是说他因为和这个体制内的东西他感觉格格不入,他没法在这里头生存,然后才被动有这个决定。」
辞职两个月后,双雪涛第一本在大陆出版的小说《翅鬼》在沈阳开发布会,不少前同事都专程去排队买书,为他捧场。栾绍华觉得,同事们在通过这种方式对这个「逃兵」表示支持和尊重。
但双雪涛对银行岁月的回忆是另一个版本。
「我就是不喜欢那段的生活,我觉得它其实不属于我的文学世界。」采访期间,双雪涛罕见地皱起了眉头。他在小说里写父母的下岗,写耳聋口哑的中学时代,写成为一名小说家后的苦闷,独独对那5年保持沉默。
在银行时他做信贷员。具体工作是,政府要向银行贷款做个项目——有时是棚户区拆迁改造,有时是钢铁企业做融资平台——需要报批走流程,他在其中负责审查。早上8点半上班,下午5点下班,典型的朝九晚五。他常常起晚了,慌慌张张套上西服,打个12块钱的车,15分钟后准点抵达办公室,摸到自己的工位坐下来。工位三面都被围了起来,有一台电脑、一台电话,Excel窗口应付突击检查似的摊着几份财务报表。
这样的生活常常让双雪涛感到恐惧,「里面暗藏的核心的那种漫无止境的庸俗其实是特别可怕的。」通常来说,六七年时间能让一个科员晋升为副处长,双雪涛干了五年整,「没有任何这样的想法」。
他向往更高更清澈的地方,但没想过怎样逃离当下,也没意识到自己可以开始写作,仅仅靠电脑里下载的1000本电子书对抗看不到尽头的时间。
「不属于这里」的痛苦太真切了,他逐渐意识到:有的人是一个李子,李子就不能长在地里。而他,就是那个被命运莫名其妙播散到地里的李子。

翅鬼想飞
在27岁之前,双雪涛从不自认是文学青年,也没有过作家梦,偏要和文学搭点边,恐怕是一点讲故事的天赋。高中好友郭庆至今还记得双雪涛给他们讲《基督山伯爵》的场景。「他不像一般说书那种,可能『嘎嘎嘎嘎』给你什么拟声词啥的,他不是这种。」语气总是平静的,到重点时音调稍微提高些,讲到主人公唐泰斯为了越狱,钻入运送神甫死尸的麻袋、被狱卒投入大海时,郭庆看到,波涛汹涌的蓝色大海似乎就在他的面前。
促发写作的动机来自现实。那是2010年,朋友转给他《南方周末》上刊载的「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征文启事,第一名能获得60万新台币,合人民币大概15万。那会儿双雪涛正为新房首付的筹措焦虑不安,这个启事像是为他指明了一条生财之道。比赛在台湾,他首先想到海峡,再想到征服和被征服,奴役和被奴役,进而想到自由。「我的名字叫默,这个名字是从萧朗那买的。」他的脑海里莫名其妙长出了这句话,它被用在了开篇,紧接着,故事开始了。
家里正因为一些家族琐事吵得不可开交,除去上班,他闭门谢客。21天,这个从未写过小说的新人一口气写完6万字的《翅鬼》,仿佛被上帝擒住了双手。他常在深夜里战栗,因为自己的想象,和自己超越自己的想象,自己给自己的意外。至今回想,「那真是太令人怀念的夜晚,一切存在未知,只有自己和自己的故事。」
中彩票似的,他真的拿了首奖,去台湾呆了10天,生活突然变得特别魔幻——见了一些文化人(之前他一个作家也不认识),出了一本书,还上了他们的广播电台。他感到命运的奇诡无常,居然把他推到了写作的道路上。临走前,他在台北康青龙文化区的小巷间乱转,地上湿漉漉的,像是刚下过雨。一家二手书店大门口的灯上,他猛然瞥见哲学家殷海光说过的一句话:「像我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没有饿死,已算万幸。」
从此以后的每分每秒,这个念头在双雪涛的脑袋里再也挥之不去:「我想吃写作这碗饭,赴汤蹈火,写出牛逼的小说,还有,尽量不要饿死。」
他那会儿尚在银行任职,就此过上白天上班、夜里写小说的双重生活。他写自己的初中时代,学费高昂,成绩落后,班主任暴戾且偏心。故事压抑了十几年,写作过程也着实艰难,「就像是中了玄冥神掌,虽然没死,不过寒毒在身,时不时就要发作。」
6个月,双雪涛瘦了五六斤,抽完了一整箱中南海,对小说苛刻到连标点也花了心思,还「傻逼呵呵」地加了注释。他把成稿命名为《聋哑时代》,小心翼翼地寄给《收获》。没能等来发表,倒是等来了编辑走走的电话:「小说先留在这里,保持联系。」泄愤似地,放下电话后,他跑去公司浴室冲了个澡,唱了半小时歌,「隔壁的女浴室听得真切,以为公司混进了疯子,就擦干自己走掉。」
如果刨去球场上一时冲动的打架,直到2012年那个夏天的夜晚,迈入而立之年的双雪涛从未实施过一桩越轨之举。
5个月前,他从因《翅鬼》结识的台湾朋友那得知了一个台北文学奖,他再次尝试着写了本书去「投标」,结果一击命中。他想了一晚上,自己「是不是应该负起写作的责任」,最后冒出来一句「操,不干了」,第二天早上就去银行辞了职。
这是这家国有大银行20多年来的第一个裸辞者,整个人事处都不知道该如何办这个手续。栾绍华为此劝过双雪涛,换相对清闲的部门,留更多精力给写作,但不要轻易丢弃饭碗。
双雪涛给的回复让他记到了今天:「人这一生最后肯定是尘归尘、土归土的,但是唯有文字,唯有踏实的创作这个东西是可以一直存续下去,相当于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痕迹,所以我想把这件事全心全意地做好。」他在银行这个牢笼里挖了一个地道,跑掉了。
辞职后的整整一年,写的东西都无人出版,也没能发表,就一直放在电脑的D盘里。《刺杀小说家》也写于那个时候。故事是一个前银行职员被雇佣去杀一个小说家——双雪涛表示这是「有意为之」,仿佛他的两个分身在相互缠斗。小说家爱去大学足球场散步,小说外的双雪涛则是去踢球。那是极大的一片土场,一旁矗着几根灰败的烟囱,冬天浇冰就成了溜冰场。写《刺杀小说家》的时候是他在此15年踢球生涯的尾声,仿佛是某种不甘在作祟,他总是要「干到最后」,从傍晚踢到天黑,踢到工作人员点灯,踢到整个场子只剩他一人。
他曾说,自己那时像是乔伊斯小说《阿拉比》中的少年,站在如丛林一样的成人世界之前,紧紧攥着枚银币在手心,感到孤独和战栗。
即便仅从工作节奏的角度来看,「把这件事全心全意地做好」也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双雪涛经历过一场痛苦的自我变革。2014年写《平原上的摩西》之时,他从银行辞职在家已两年。起初,一觉能睡到11点,起来吃了早午饭,坐在洗手间看几行书,就又有了午睡的念头。沈阳的冬天白昼极短,有时双雪涛起晚了,窗外漆黑一片,似乎天根本没有亮过,仿佛狗熊陷入了一场错过阳光的冬眠。
为了防止「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长出毛皮」,他开始定闹钟,甚至还幻想过写作之前穿上制服打上领带,或者给书房装一个打卡机(就像村上春树做的那样)。这部3万字的中篇小说写了七八稿,几乎占据了他2014年四分之三的时间,最后一稿是修补了一处醉酒的细节。写的是他童年根据地之一的艳粉街,那是沈阳市中心的一片棚户区,从空中俯瞰,2000多户平房如蚊香般一圈圈展开,有煤山、矿场、高粱地,还有充斥着刑满释放人员、诈骗犯、妓女、残障人士的左邻右舍。
像是一场旷日持久而要求太多的恋爱,为了防止被这个故事拖拽得越陷越深,双雪涛搬到岳母家,清晨再坐十几站公交车回去,把自己家当成工作室,写到快精疲力尽就赶紧收手。但每天晚上,他总还是惦记着那个独立躺在空房间电脑里的文档,「我听见那空间里的心跳声,怦怦怦怦,不太规则,有些力量,就像我从小生长的这座城市,永远在脚手架和挖掘机的包围之中,但是她还活着。」
他全盘接纳写作带来的快乐和痛苦。就像他在《翅鬼》里写的,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雪国,带翅的婴孩被送入井下劳役,成为终生囚徒,但他们不甘心,打算凿开一条通道,飞离雪国。
翅鬼飞起来了,再不愿自断双翼。

最纯粹的
在位于和平里北街的办公室里,双雪涛的两位责任编辑罗丹妮和刘婧为他的「纯粹」和「复杂」争论了起来。《飞行家》的封面写上了「最纯粹的小说家」这一行字,刘婧印象中的双雪涛平和、单纯、不计名利,而和双雪涛接触更多的罗丹妮则说「他的目光里面会让我感受到一种并不是那么容易亲近的东西。」
一位作家朋友把双雪涛的这种矛盾称之为两个界面,一个是友好的界面,另一个隐于人后,是身为作家的孤傲的、自我的界面。双雪涛觉得,那个友好的界面只是个壳子,「这个壳子经常用于挂挡,就像汽车挂挡,但其实内核还是一个比较骄傲的人。」
只要是和写作有关的一切事务,双雪涛就容易挂成另一个挡位。罗丹妮记得,新书的封面文案和目录顺序经历了数次调整,以至于快定稿前,双雪涛还特地跑了一趟办公室。没带包,也没带烟,空荡荡地坐在那里,也不说话,就拿着铅笔在目录上涂涂改改,改完后还郑重其事地誊抄了一遍,用手机拍了照。
双雪涛认为自己的谨慎没什么大不了的:「小说集的摆放其实是个建筑学,就是这个房间要冲阳,这个房间冲正北、冲南,你不能一把随便摆,那你把马桶挨着厨房肯定是不行的。」
小说家的职业性除了规律写作外,「他的作品是不是一个好活儿,是不是有职业的水准」同样是个重要的判断依据。据说为了清除小说中的赘肉,海明威会站立着写作,双雪涛想了另一个办法,唱着歌写。即便跑调得厉害,也要放松,保持舒适的手感。就算是中篇小说,他也会将其当作简短的长篇小说来写:「锻造叙述,洗净尘垢,压紧命运,如同训练一个肥胖的食客变成一个瘦削的士兵。」再就是不停修改,大多用十几天,每天看几遍,「朴素」是准绳,「写时那些自以为机灵的比喻,那些自以为含义丰富的场景,有时候一个动词就可以更好,所以十几天主要是寻找词语,卸掉粉底和唇彩。」
但也有人在这「纯粹」下嗅出了铜钱味。豆瓣上有双雪涛的老读者评价《飞行家》:「新世界大门打开后的迷乱,电影业人和钱带来的眩晕。一本经常让人想到电影场景、剧本、剧组的小说,失去了古朴与野蛮的冲劲,模仿、因袭掺杂着叫卖,像生存在橱窗里的模特。」
和双雪涛的三次见面都在北京丽都饭店旁的一家西餐厅。这里聚集了北京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尤以电影人居多,双雪涛常在这里谈工作或踢球。「我那边有熟人,过去打个招呼。」餐厅人来人往,他不时会碰上一两个熟面孔。
一次闲聊期间,双雪涛接了一个越洋电话。放下电话,他还是感到难以置信:「一个美国的做电影的顾问,说是要把我剩下的所有没卖出去的作品(版权)全包圆了。我说这他妈是什么,这是什么玩法。」三天后,记者再次向双雪涛确认故事的后续,「当然是不可能的嘛,那也不是卖白菜,对不对,不是东北冬天要卖几百斤白菜。」他用轻松但认真的语气说。
写作曾是双雪涛逃离世俗生活的乐园。他去北京,本是为了离纯粹更近,但事实上却更为俗务相累——每天都有无数等待回复的微信,每月都要至少准备一份讲稿。过去双雪涛不修边幅,常蓬头垢面、挽着裤腿在外走,现在迫不得已要登台,只得在镜子前把自己拾掇一番,「一时无法相认」。初春,他去广州录制「一席」的讲演,前一晚飞机延误到凌晨4点落地,睡了两个小时,又强撑起来直奔彩排现场。一上台,白炽灯闪得晃眼,底下五六百人在那儿守着,「腿一直在哆嗦……真的是讲了上句忘了下句,很多东西都是靠原始的本能讲的。」他对自己的表现失望极了,有些苦恼自己「应了一件从没干过的事儿」。
他越写越慢,2016年成为产量最低的一年。相比中短篇,长篇统一的文学腔调需要屏气凝神的漫长过程,在此期间,肉体或精神上的一点微小变化都会干扰到他。「我一旦这个精神头一散吧,就效率特别低」,因此,他梦想中要写的100万字大长篇只能无限向后推迟。
来到北京,作家双雪涛有些恍惚:自己怎么混到这个圈里来了?他在创作谈里写:「看某些名家招摇而过,穿行于各种局面之间,其实已丧失与世界交谈的能力。看某些新作家低头垂目,似乎清醒,转身便与人合影,琢磨着找谁写推荐语,为研讨会奔忙,似乎也无甚大趣味。」
真正在他北京的朋友圈里的,数来数去只有六七个。最常聚的都是电影人,路阳、张骥、《白日焰火》的导演刁亦男,几个老爷们一块去涮肉馆,热腾腾的羊肉就着啤酒吞下去,局上不聊闲篇,就聊电影和文学。几个导演最爱给双雪涛推荐电影:「沟口健二你得看,除了小津和黑泽,这个也很厉害。」聊完附送张碟就散,下周接着约。
得奖后「迷迷糊糊膨胀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过。通常会持续两三天,最多一周,紧接着又会重新陷入焦虑:「我操,我就写这玩意儿还没有写完。」张骥记得,有时聚会话题转到这两年大伙的变化,喝了点酒,双雪涛总会红着脸、絮絮叨叨地说:「这变不变,我就是写小说的,那我就是写嘛。」他曾在朋友圈发过:「小说家还是适合倾听,上台之后嘴角都有点表演的曲线。」像是某种自我警醒。
「又是玄幻,又和电影拉上关系,局面已打开,顺这路数走下去,不说前途,至少会步入钱途。」从《翅鬼》这样的类型文学发端,沉下来转入严肃写作——作家田耳评价双雪涛的写作是一个「反熵」的过程,「这是一个写作者听从内心召唤的选择。」
「老哥儿一个,独资公司,一个人。」双雪涛珍惜这样的状态,他的职业不是别的,就是小说家:「希望自己能像小说家一样存在,而不是别的什么玩意,单纯的身份在现代社会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但是恐怕是我唯一能向往的虚荣。」
那小说家是谁?双雪涛思忖该是滑稽的人,像是抗战时期日本人打进来,一群伶人穿着戏服,扮成秦琼关公骑着战马去抵抗。世道怪,人人都贴地匍匐,但他有翅膀,还能再飞一会儿。
双雪涛认为,《像小说家一样写作》可以帮助到两种人。
第一种是 有一定基础的人 。「但他们在纷繁的世界里头,被好多东西诱骗,没有找到自己的路,没有找到自己的方法。」他们需要学习该如何按照自己的心性写。
第二种是 起点并不高的普通人 。但是通过《像小说家一样写作》,这些普通人可能突然间试着写了一篇小说,双雪涛说,“也可能一辈子就写这一篇,或许还会写,这都有可能。”
原标题:双雪涛:我想赴汤蹈火,写出牛逼的小说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