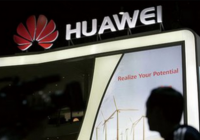我小时候常见走街串巷卖丁丁糖的人。
坐在小板凳上,面前两个竹编立筐,上边儿一个个白色硬糖叠叠相交,糖面上大大小小的孔隙,乳酪似的。卖糖人左手一张弓形小铁板,右手一只小铁锤,隔不多久互相一撞,“叮”地一声响——所以叫“丁丁糖”。

要做丁丁糖,难,也不难;难是工艺,不难在用料。
将大麦用清水泡住,发出麦芽后,和蒸熟的糯米拌匀,装在干净的大缸里,等它化成糖浆。糖浆出来后,再倒进锅里慢熬,一边加入炒熟的芝麻大米粉。眼见水量一点点下去,糖浆浓稠成饼,就取出来挂在木钩上反复拉扯——一拉三寸,二拉三尺,三拉不得了,长长一条白练,手一撒,就冲天而上,复又重重落下,回到卖糖人手里。
那卖糖人一接一绕,便又缠上了木钩,眨眼功夫,又长三寸,再长三尺...如此反复,真是绝活!等这糖条变成乳白色状,就将它从木钩子上取下来,放在撒了大米粉的案板上滚条切块,成了平时常见的模样。

这么一说做法,很多人就明白了:丁丁糖其实是麦芽糖的一种。
古代也有麦芽糖,只是不叫这名字。
糖
麦芽糖古代人叫饧,也叫饴糖、花饧、胶牙饧,历史很久,但丁丁糖的这种卖法,至早要到东汉末年、魏晋之初(约公元184年-220年)了,那时候叫“吹箫卖饧”。
这里的箫,不是那种细长的洞箫,而是小竹管编成的排箫,声音没那么幽咽低沉。卖糖人一边走,一边吹箫,跟现在板锤相撞一个道理,都是勾人魂儿买糖的意思。
卖饧糖的人,每年两个时候生意最好。
一是腊月,“二十三,糖瓜粘,灶君老爷要上天”,老百姓祭灶神前后。
灶王爷是谁,其实谁都弄不清。有人说他是火神祝融,因掌管的火和生灶做饭有关,所以祝融就兼任了灶神一职;也有人说他是炎帝,炎帝以火德治天下,死后登仙榜,成了灶神;还有人说灶王爷其实是黄帝,因为他教会了老百姓做饭...总之,都没个准数。不过,这也不打紧,反正老百姓只要知道,腊月二十三要祭神,祭的这位是灶王爷就对了。

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人偏就要较真,光有“灶王爷”这么个称呼可不行。秉着“脸即一切”的时代精神,司马彪(?—公元306年)正儿八经地跟人掰扯:你们总以为灶王爷日日夜夜受人间烟火气儿,熏得面皮黝黑,其实人家容貌姣好,远望过去,一身耀耀的赤色衣袍,绝色美人似的,以后可不许胡说八道了!
到了萧梁,宗懔(约公元501年-565年)写《荆楚岁时记》,又给灶王爷添了名姓:姓苏,叫吉利,从他嘴里讨的也是吉利,所以得给他进饧糖,甜蜜蜜地黏一嘴儿。
玉皇大帝问:“某家某户,今年做了什么好事儿,什么坏事儿?得受什么赏?挨什么罚?”苏吉利嘴里糖块儿还没化干净,吃人家嘴短,只好眯着眼睛笑呵呵,“都好,都好”!
老百姓借他的喜气,也吃饧糖——魏晋南北朝人叫胶牙饧,就着屠苏酒。这习俗延续下来,唐代白居易写诗,还有“岁盏后推兰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劝人家喝酒吃糖的作法。
另一个卖饧糖的好日子,是在四月初二三,过寒食节的时候(魏晋南北朝还没清明呢!)。寒食节,节如其名,得禁火,而且还不只禁一天,整整三日!煮不能煮,煎不能煎,吃什么嘴里都没味儿!怎么办?熬好大麦粥,再在里边儿搁三五块饧糖,搅一搅——宋祁写诗, “箫声吹暖卖饧天””,心中若有甜丝丝的活气,冷粥也能下大三碗。

▲宋·苏轼《寒食帖》
饧糖是人人都买得起的寻常物,相比起来,石蜜就金贵了。
譬如魏文帝曹丕和孙权往来(公元220年-226年),送他百斤石蜜;西晋尚书令荀勖(?-公元289年)身体羸弱,晋武帝赏他五斤石蜜,这些都是要被记入史书的大事儿。
魏明帝曹叡(约公元204年-239年)还专门诏集群臣,郑重问过:“南方的龙眼、荔枝甜,还是西域的葡萄、石蜜甜?”结论是葡萄石蜜更甜。
石蜜当然得更甜!
《齐民要术》里说了,将交趾(今广东、越南等地)的甘蔗榨汁后,煎而暴晒,不多久就会凝成块,结了冰似的,又像石头。为什么非得交趾的?阳光充足,甘蔗醇、甜,有味儿!
将它切成一粒粒棋子大小,放在嘴巴里一抿,顿时化成一汪甜水。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说得更明白:什么是石蜜?就是白砂糖!凝成块儿,硬的跟石头似的,就是冰糖。
虽有这样的记录,但石蜜究竟是什么,后世说法其实依然不太统一。
有人说,石蜜的确和冰糖一样,是甘蔗做的,但它工序要比冰糖复杂,是巴蜀那边儿的精炼糖。——别看现在巴蜀以吃辣闻名,魏晋南北朝时,他们是吃甜的,煮鸡烹鸭,都得搁蜜。
因爱吃甜,所以在制糖上很下了些工夫:先挑那种轻掐一把就出水的泡甘蔗榨成汁,再在里面放水牛乳、米粉,搅和均匀,摊在锅里煎成金灿灿的薄饼,盛起来趁热气放一块儿在嘴里,糖酥酥里带着乳香,“嗨呀,好巴适哦”!
蜜饯
还有人说,石蜜就是蜂蜜,用处很广,其一就是做蜜饯。
魏晋南北朝时,水果品种已很多,什么桃啊、李啊、杏儿啊、梨、葡萄、石榴、枇杷、甘蔗、杨梅、椰子、槟榔、橄榄、龙眼、荔枝....数不胜数,可惜只在应季那几天。过了日子嘴巴馋,心眼巴巴儿地想吃,哪儿有啊!嗨,怕什么,有蜂蜜哪!用蜂蜜把它们腌好,做成蜜饯,想吃多久吃多久。
譬如葡萄干。做葡萄干,是要用油烧的。紫得发亮,皮儿快绷开的极熟葡萄堆在面前,剪刀咯吱咯吱,摘叶去蒂,再一股脑儿滚到锅里,一层层浇上蜂蜜,最后大撒几圈油,放在柴火上熬。不多时,点滴蜂蜜化开,油也消下去,在锅里滋滋响,烟色升腾,全是葡萄甜香。再过一阵,糖水浸入果肉,又被火气烘热,一点点瘪下去。等停火阴干,随拣一枚入口,那甜得!
还有梅干。梅子因自带酸味儿,所以古时候多用它调味,跟醋似的。核初成的时候就摘下来,晚上用盐水大泡,白天曝晒,反复十次,就能用了。但四川那边儿喜甜,总嫌这梅子调味太酸,便又有了另一种制梅方法:把大梅子挑出来剥皮阴干,先用盐水泡两日,再将盐水洗了,改放在蜂蜜里腌。每过几个月就换一次蜜,就这样搁一年,也还是新梅子的味道。
这样的蜜饯盐梅,不光能拿来作点心,若不小心喝多,昏昏然不知今夕何夕,喂他二十多枚蜜浸的乌梅,立马清醒。初入口极甜,人还晕着,稀里糊涂乱咬一气,厚实梅肉烂在嘴里,酸味飚迸,直冲脑门儿,人连连打上几个激灵,便睁开了眼。南陈的永阳王陈伯智(约公元540年-618年)有一回喝醉,就是用这法子醒的酒。
除了蜜饯,魏晋南北朝时,还流行一种果麨。这字儿不好认,但说简单点,就是现在酸梅粉、果珍一样的东西。想吃时,用水冲开就行,酸酸甜甜的味道。但当时通常不单喝,是和米粉混拌在一起,当做远行外出时的干粮。
还有果醋。将落在地上自然烂熟的桃子搜集起来,放在大瓮里密封上,七天后打开一看,烂得透透的。这时,将桃皮和桃核都去了,再次密封,不多久,就自成桃醋了。做菜时滴上几滴,酸里带着桃子的甜香,饭都能多吃几口。现在陕西那边儿卖柿醋,有些用的,就是这样的古法。

柿醋制作
做蜜饯,制果麨、酿果醋,当然可以保存水果,不过这些方法,都有些麻烦,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那当然也是有的:直接放在太阳底下晒,等水分蒸尽,就是果干,拍拍泥土,捡起来就能吃。
话虽这么说,真晒果子时,依然讲究得很。
例如做枣干。枣是新石器时代就有的食物,但魏晋南北朝时,因有了嫁接新技术,所以对果子要求也高了。皮儿光洁,色赤红,肉厚实,手捏上去还得软,这样的枣儿,才算好。
有了好枣不算,还得有好地。来回扫几遍,一粒草屑都不能有——草令枣潮!所以得清干净。收拾好地以后,便搭木架子,木架子上放竹帘子,竹帘子上搁枣子,一层一层,都是为了隔水气,怕坏臭。
枣子放上去后,仍不能松懈,得时不时给它们翻翻身,拨聚在一块儿,又打散开来,一天得来回折腾二十多次。就这样过去五六天,把红软的大枣儿挑出来,挪到高橱柜子上再晒....这样反复拣择的枣,个儿大肉厚,阳光将甜都晒沉了,能不好吃?
若将这样的甜干枣倒在酒里,装在坛子里密封,能放好多年。想吃的时候,捻一个放嘴里,初咬酒气辣冲上颚,顺着鼻子直刺天灵,再咬枣香漫口,喉头一动,枣味儿酒味儿滚滚下肚,不多时就醉熏人了。
西晋惠帝年间,皇后贾南风害愍怀太子司马遹(公元278年—300年),用的就是这种醉枣。贾南风先借口皇帝生病,让司马遹入宫探望。司马遹奉旨入宫,却 “只管远远儿地等着去”,被带到了别室。侍女们鱼贯而入,端了一盘又一盘的醉枣喂他吃。
不多久,司马遹就醉了。趁他昏昏然,贾南风让人握住他的手,誊了一份早写好的文书,转又拿给晋惠帝和大臣们看。这文书十分霸道,说要杀晋惠帝,杀贾南风,等他两个都死了,自己就好登基做皇帝。如此谋逆,有几个朝臣敢为司马遹说话?因此等司马遹酒初醒,就已成了庶人之身,被关到金墉城里去了。
这还不算,正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司马遹虽然失势,但他一天不死,贾南风就一天不能安心。没过多久,贾南风又让人去金墉城,逼司马遹服毒。性命攸关,司马遹当然不肯轻易就范,只是那时他已被饿了很多天,身体虚弱,强撑着逃到厕所里,最后无路可避,被人活活用药杵打死,年仅二十三岁。
我每读到愍怀太子传,心中就有痛惜。司马遹少时聪慧,他爷爷晋武帝司马炎曾赞他雄才大略,极善权变,将来必为明君。谁知造化弄人,被认为有司马懿遗风的司马遹,长大后性情乖张,又身陷政治风波,终究早夭了。
水果
蜜饯果干虽好,若能择拣,当然还是愿意吃新鲜水果。
魏晋南北朝时,果树很多。城墙边儿上、宫廷苑囿、世家庄园、甚至寺庙住宅,到处都能见到果树。东晋孝武帝(公元372年—396年)修新宫,城外护城河沿岸,全种上了桔树;宫里疏密有致,栽的是石榴。每年四五月份,桔花盛开,雪白团团,洁清可爱;还没谢却,宫里榴花似火,就艳艳绽放了,真可应得“如火如荼”四字。等到花谢,两树结果,一橘一红,又都是喜庆的好颜色,点染城头宫内。
孝武帝种桔,多半是喜欢它好看,三国吴(公元222年-280年)的李衡,可就指着它养家了。他曾经让人在武陵(今湖南常德)种了一千多株桔树,临死前叮嘱儿子:“你娘常常说我不会赚钱,所以家里穷成这样。但我在武陵那边儿种了一千多头木奴,等它们长大结果,每年能卖数千匹绢,家里就再不用愁了。”
因这样的故事,所以后来又把桔树叫做“木奴”。到现在,湖南常德那边儿的橘子还很好吃。皮薄而甜,白丝浅,肉瓣厚,咬一口,果粒分明,大半不酸,吃完一个,满肚子沁甜。

李衡这样的人,当时并不少。很多人都看到果树带来的商机,争先恐后下海经营。
譬如竹林七贤的王戎,于果树鉴别上,从小就胜人一筹——他六岁时,有一次小伙伴们在路边儿玩耍。大家笑闹很久,口干舌燥,抬头见路旁李树上结了不少果实,便哄然过去,想采来吃,唯王戎他老人家岿然不动。有与他相好的,扭头叫他:“再不去,李子都被别人吃光啦!没你份儿了!”王戎嘴一撇:“这李树长在路旁边儿,还能结这么多果,肯定因为实在太难吃了。”
小伙伴们当他放屁,蹭蹭蹭上树将李子摘了个遍,放在嘴里一咬,涩得牙都麻了!因有这份儿眼光,王戎长大后自然做上了果树生意。他精明得很,怕有人借种,每次都要亲自挨个检查,将果核挑出来,才准家人拿到市场上去卖。

唐 孙位《高逸图卷》中的王戎
王戎一代名士,居然下海做生意,沾染一身铜臭,叫后世道学家很看他不起。然而当时佛门方外,也觉得这红尘闹热,果树繁盛,很有亲切,纷纷撩起僧袍种果树。卖果子的钱,成为寺庙一大重要收入来源。
出家人实在,既靠此营生,那种出的果子,质量也很经得起考验。洛阳白马寺一个甜石榴,个头极大,秤上一过,足有七斤!这是送礼的佳品,得到的人大半不舍得吃,攒着还人情送给下家,有时要辗转好几处,所以童谣说:“白马甜榴,一实值牛”,说它金贵。
还有报德寺的含消梨,戳着硬,咬一口,全是水;若拿竹竿子将它们打下来,从树头到地上,一眨眼,就散化了——每个也有十斤重。华林园里的仙人枣,足足十五厘米长,两手捧住,头尾都在外边儿,枣核针似的细,甜那自然更不必说。还有敦煌的大瓜(据说瓜肉沙而甜,足有枕头那么大!)、魏郡的好杏儿、承光寺的柰林(即今天的绵苹果)……
噫吁嚱,时乎久哉!这些甘如饴的水果,竟都已难得一见,成了白纸墨字儿的故物,唯能长叹一句:独恨不逢甜榴果,晚生不见胖枣来!
原标题:吃辣成风的川渝人民,以前竟是吃甜党?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