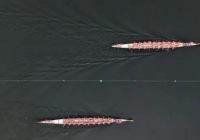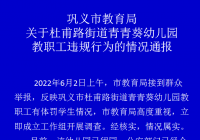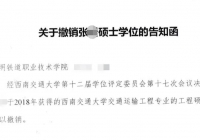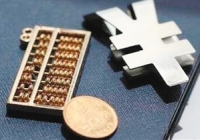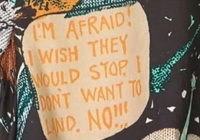她从端午来
谭鑫
取两叶芦苇轻裁,一卷曲如斗状;互托擀糯米填实,一拧握以成形;拴麻线为之侧绑,一系粽悬于庭——在这一卷、一拧、一系之间,端午的盼头循香而来。
好多事情都是说来简单、做起来难,包粽子也是一样。
哪怕我能说得条条是道,但实际操作起来,往往也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但是,无论是母亲,亦或者奶奶和外婆,在为期每年一次的实战中,却总能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给家里的“观众们”带来惊叹而无悬念的观感体验。
在手比脚笨的我看来,包粽子也是要看性别的,至少在我家便是如此。父辈们一到端午,便如约好一般守望在旁,即便是在最家常的白米粽面前,充其量也是个打杂递水的伙计,不敢轻言下手;更有甚者如我,只能充当卖力叫好的角色,叫声“六六六”便感觉参与了忙活儿。
包粽子的表演,注定是母辈们的绝活儿。她们行云流水般的手法,助长了父辈们心安理得地当好观众,赚得我只能做个四体不勤的继承者。
而每当我摆出小迷弟的笑脸,想用过度的褒扬,去赞美那些堪比卖油翁盖铜钱倒油滴水不漏的表演,企图能够让母辈们开口吐露获奖感言,她们都会轻飘飘地用一句类似于“无他!唯手熟尔”的话语把荣誉架开。显然,持家多年,一个粽子的具体重量早已暗称于心,不会因轻言重语而摇摆。
直到有一天,我亲手从她们手中接过筷子和粽叶,将平常包一个粽子的时间拉长了十余倍才勉强成型后,我才终于懂得——纵然理所应当,但却千变万化;即使绝世稀有,倒也稀松平常,这些不足为外人多言的“家常”,我愿私称之为“母亲的魔法”。
高三那年端午,恰巧在高考前一天。
在那个可能是人生中第一个没放假的端午节,我们早早地聚集在临时教室里,一如往常地准备着复习。其实当时已经无心做题,满脑子都是明天的考试和临阵前的兴奋,人人抱着“站完最后一班岗”的心态坐在那里,不知为何那天早课没有班主任把守,更不知为何班里竟也安静得出奇。
那是人生中为数不多的绝妙体验。虽然各自的心情像窗外散不开的云,但时间在我们手里却统一的、只留下了翻书的沙沙声。
不一会儿,班主任“姚妈妈”和同学妈妈两位“母亲”一起出现在了教室里,她们额头都带着汗珠,手中却端着一箕粽子,泛黄的粽叶裹挟着的糯米正成熟地往外冒着热气,教室里瞬间温香满溢······
“今天过节,和何妈妈一起包了点八宝粽,刚刚煮好,同学们都来尝尝······”一一分发下去后,班主任没忘补上一句“吃完抓紧复习”。很多同学拿着那颗粽子,突然联想到班主任早课的缺席。
从涪高中毕业后,我再没吃到过那个味道的粽子。当时我便在想,如果没有那个粽子,我会不会遗忘掉这样一个端午节。
但我愿意相信,岁月不乏遗忘,但感动终将弥新。
在长沙读书的日子里,有次从汨罗附近的地方拍完大学作业回校,正好是端午节前后。在寝室做素材剪辑忙到夜深,只知道睡意来了又走,窗外亮了又暗,如青春中总有的某个片刻,分不清黑夜还是白天。
睡意朦胧之中,突然收到一条来自家乡的短信,我以为是端午祝福,没想到是:“我买了到长沙的票,已经上车,明天早上到。”
想到她第一次出远门,像青春忽然惊醒,一下子睡意全无。
第二天很早,拖着厚厚的眼圈被闹钟赶下了床。刷牙、洗脸、洗头······在黎明前的夜色里连奔带跑,终于赶上了第一班开往火车站的车。等到接近中午,才从列车晚点的人群里认准了她。
走在回来的路上,看着街边锅炉里那青绿的物什,突然想起前些天汨罗江附近的预热,记起了那天刚好是端午节。
“想吃粽子吗?”我突然想起还没吃早餐。
“没胃口······”一夜未眠她有些哈欠连天。
“不过,我给你带了几个来。”她翻开手中那个小小的包,里面竟然藏着几个大大的鲜肉粽。
这似乎便是她此次旅行的全部意义。
而那和她一起穿山赶海而来的粽子,蓦然地却散发出一股家的香气······
近日早上上班,突然收到了一包粽子。打开一看,有白米粽、八宝粽、鲜肉粽······在这一白、一素、一荤之间,端午的回忆扑面而来。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版面欣赏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