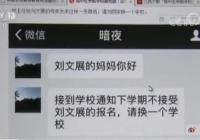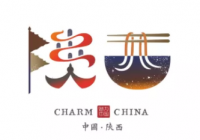纪慈恩,临终关怀志愿者,十多年来一直跟“死亡”打交道。图片来自网络
新京报—剥洋葱people消息,“死亡是生命一个非常正常的过程,它从来都不是突然来到我们生命中的,探索和亲近它可以看到生活中我们很难看到的东西,它是反映生命意义的一面镜子。”
纪慈恩把这句话,写在她个人微信公众号的介绍里,30岁的她,比同龄人,经历或接近了更多的死亡。
掀开这个序幕的,是10年前,她满足了罹患肝癌好友的心愿,在荷兰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当抱着朋友的骨灰回国后,她被指责、唾骂,“杀人犯”、“凶手”、“会遭报应”。
“为什么人们恐惧死亡?”她一直想找这个答案。她曾走进了孤儿院、福利院,做了10年义工。其间,她还做了临终关怀志愿者,多年里,陪伴30多位老人走过最后的生命时光。
“其实,让我们恐惧的不是死,而是对于死的看法。”3年前,纪慈恩建立了体验死亡工作坊,想让更多离死亡还很遥远的人,提前思考这个终极命题。
纪慈恩的名字,是她自己起的——“纪念生命里收获和付出过的慈悲与恩情”。十年时间,她一直在和“死亡”打交道,身边每一个人的离去,改变了她对死亡的看法,也改变了她的人生。
以下内容为纪慈恩口述。
(一)
十年前,我19岁,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医院,签了一份安乐死同意书,改变了我整个生活的走向。
安乐死的对象,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默默。她在荷兰留学,被查出肝癌,2006年冬天时已经需要靠大量止痛针维持生命,医生说,她最多活半年。
默默希望我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去荷兰陪伴她。她父母很早离异,一直抚养她的奶奶也去世了。那是我第一次出国,看她躺在异国的病床上,被痛苦折磨。
她希望我能签下那份安乐死同意书,在荷兰,安乐死是合法的。
那时候我觉得,活得再痛,也好过死。当地医院规定每天只能打两针杜冷丁,每一针可以止痛四五个小时,可默默只打一针,最痛时,她用牙咬自己的胳膊,松开以后,满口都是血……
最后,我还是签了同意书,安乐死药物注射进她体内。
按照规定,我必须离开病房。趁医生不注意的时候,我提前把她房间半落地窗的窗帘,拉开了缝。
我站在窗外,能看到她的脸,药物缓缓进入她的身体,默默很平静,甚至脸上带着喜悦。我永远忘不了,她看向我,用手指贴着脸,比了一个V字——胜利的那个手势。她是告诉我,自己终于解脱了?还是告慰我,我一定可以战胜之后内心的折磨?
我哭着把她骨灰抱回国。
追悼会上,大家说我是凶手,要遭报应,没有权利结束别人的生命。
后来一年,我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拉着窗帘,不和任何人讲话。声带很久没用,已经变了,原来细细的,变成嘶哑的。我被医院确诊为“PTSD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
默默的死,是我第一次被拽进死亡这个漩涡里,拔不出来。
直到心理医生带我去了北京,去到默默父母离异后,她曾待过一段时间的孤儿院,和一个个小孩子相处,我的心结才逐渐解开。同时,我去做心理治疗,一遍遍重复回忆我和默默分别的时刻,直面伤痛。直到最后一次,我已经复述了7个月,讲了65遍。大半年后,我慢慢恢复了正常生活。

纪慈恩在孤儿院做义工。
曾有一个四岁的艾滋病小孩告诉我她对死亡的理解,她觉得她死后一定会很幸福。就像人们买汉堡包一样,要先付钱,才能得到。她认为,每天躺在病床上一定是在“付账”,所以她死后会很幸福。这刷新了我对死亡的看法,成年人理解死亡,总是被太多东西牵绊。
我想找个答案,为什么人们恐惧死亡?所以,才做了临终关怀志愿者。这么多年,我陪伴送走了30多位老人。在台湾,病房里,老人家们唱歌、插着氧气打麻将、淡定地面临死亡。其实,让我们恐惧的不是死,而是对于死的看法。
现在,我仍然会想到默默,是想念。有时候也会流泪,心里不想经历这么多,宁愿我们都是平凡的女生,在过平凡的生活。可如果不是和她的故事,我的人生不会做现在坚持的事情。
(二)
这些年,做临终关怀志愿者,我接触了很多老人,他们对生死有自己的理解。不是说,老了就有了智慧,而是在临近死亡时,人已经被逼得,把很多事情想得明白了。
(编者注:临终关怀,这个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被引入我国的概念,致力于提高即将逝去患者的生命质量,通过消除或减轻病痛与其他生理症状,排解心理问题和精神烦恐,令病人内心宁静地面对死亡。同时,帮助病患家人承担一些劳累与压力。)
有时,我会带着老人们写清单,一条条记录下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普遍想做的,是回到老家或是曾经当兵插队的地方去看看,那些地方,他们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年纪。受限于身体条件无法远行,我们会把他们想对那些地方(的人)说的话录音或录视频。他们会讲述自己一生中故事,而我负责写传记。
几年前,在北京我服务了一位林奶奶,80多岁癌症晚期。她常常跟我说:“生命有它的定数,我们要承认,生命就到这里了,我们就允许它到这里。”癌细胞扩散后,她开始吃止痛药、打杜冷丁,疼痛感尚处可以承受的范围。
和家人的分歧出现在化疗时期。她经常来医院,见过一些化疗的老人,为了方便照顾,穿个内裤盖条单子,身体里插导管。林奶奶是个体面了一辈子的人,她不想那样。尝试了第一次化疗,她的疼痛感很强,开始掉发。当发觉自己和其他人化疗后的状态一模一样后,就开始抵抗治疗。女儿不理解,逼她继续化疗,林奶奶用自残来抵抗,女儿逼一次,自己就在颈动脉割一刀。直到她割到第四刀,她的女儿才含泪不得不放弃。
一般从早上9点半到吃过晚饭,我都陪在林奶奶身边,和她聊天,她会把内心的东西跟我讲出来。她对老伴儿愧疚,因为老伴儿重病时,她也像女儿那样,逼他治疗。老伴儿是个没什么脾气的人,没有表达太多的不满。
林奶奶快不行的那段日子,靠在窗前,就说了一句:终于要死了。很多的老人都表达过类似的情绪,似乎在等待死亡的解脱。她的话刺痛了我。我陪她那么久,其实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其实,做临终关怀,理理发、讲笑话、读报纸……这些都是浅层的,老人们需要的是高质量的陪伴,你能让他们对你敞开心扉,说出自己心底的东西。
从2009年开始,我越到后面越发察觉到,临终关怀里所有内容都有一个基础,就是身体少有痛苦。当然,在具体过程中,志愿者可以帮助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对方有遗憾、有心结、有放不下的事情,可以帮助他们去做。但如果,病人已经疼得快死了,他还能顾得上这些事吗?癌症晚期的病人,疼起来,他们要靠药物辅助,每天都在痛。身体难受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心情去聊天、从心理上舒缓自己。心灵关怀,更多是志愿者自己觉得,提供了陪伴。
曾陪伴过几位老人,前一分钟还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讲话,之后就闭上眼睛去世了。渐渐地,临终关怀里照顾的老人们离世,我都习惯在他们曾经的病床上躺一会儿,闭上眼,体会他们临走时的感受。
当时,我想要做一个事情,它可以是一个课程,或是一个活动,让普通人去体验、思考死亡。2014年我建立了体验死亡工作坊,全国上课,重点在深圳、武汉、昆明三座城市,1-2个月一期,期间还去了台湾、香港。
假如你还有最后10分钟,你会在遗嘱上写下什么?我希望能推广“死亡教育”,让那些暂时远离死亡的人们,提早了解死亡。

纪慈恩。
(三)
默默离开十年后,整整一个十年,命运又跟我开了个玩笑。
2016年11月底,我女儿去世了。
真真是我收养的女儿,她出生后被查出患有“法洛四联症”,一种儿童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50%的患者死于3岁内,70%-75%死于10岁内。而我陪伴了她9岁-17岁的时光。
她没有安全感,遇到我之前,曾被辗转送过五六家福利院,变得敏感易怒。福利院里,她最信任的人就是我。后来我收养了真真。
我从北京到昆明,再到大理生活,真真一直跟着我。她变了,在学校帮助别人,为受欺负的孩子出头。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她的生命会在十几岁时结束这个结果。差不多,我暗暗用了5年的准备,来面对她的离开。其间,我们还是做了手术,做手术本身也没有报根治好的希望,只是为了不留遗憾。
真真担心手术费用的问题,需要五六十万。我和她说,可能手术钱花了也失败了,但我们至少努力过,不后悔。最后关于手术,我们达成了一致。
了解死亡,是因为人需要知道怎么去面对它。做好了面对死亡的准备,也不代表它来临时没有痛苦。真真在世时,一直是个很努力在活着的小孩,她离开后,我开始旅游,那也是她的一个愿望。我想在不同的时空中,继续和她共存。
现在在大理,我找到下关的福利院做义工,照顾那些因先天性疾病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云南福利条件不像北京,但我觉得,可贡献的空间,更大了。
如今我觉得死都是小事,活着才是大事。当下是大事,其他都是小事。死亡只是人活着的,生命最后的结果,只能面对和接受它。
体验死亡工作坊中,六七成的环节以体验为主。比如,会用一些音频,把体验者代入飞机即将失事的情景里,在那一刻,内心的感受是什么。它就像一个死亡攻略,人总会走到死亡这个地方,但过程中,如何应对处理、调整心态,可以被提前训练。
这些演练,和生命中经历的死亡当然是有差别的。它的意义不是在教我们临死前要怎么办,而是内心去经历一次对死亡的焦虑与恐慌,借由这些,去重视自己该怎么好好活着。
(原标题:与死亡打交道十年后,我明白了该怎么好好活着)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