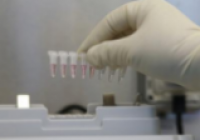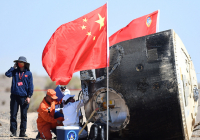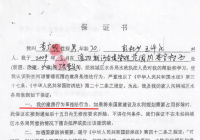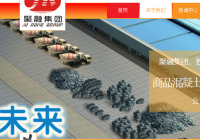▲农民工在一处建筑工地门口寻找工作 图/视觉中国
被“清退令”挡在工地外的是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尚未兴起时一头扎进工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图景添砖加瓦,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工地的发展奇迹。
现在,到了他们离开的时候。刘修田是幸运的,他在工地上找到了辅助性的岗位,更多的人离开了工地,只能回家干零活或种地养老。
土方车淌着水滴驶出工地大门,清洗区后方暂时没有车在排队,刘修田放下高压水管,坐到一边的椅子上,边走边从烟盒里掏出一根烟,抓紧时间吸了两口。
刘修田的工作是冲洗土方车,以免它们将工地的灰尘带入城市主干道。他所在的杭州市Z工地将要建成一座大型商用写字楼,这几天正在挖地基,土方车进出频繁,一天出入约上百次。冲车的时候,刘修田偶尔叼一根烟,但烟头容易被水沫打湿,抽得不痛快。
跟以前在工地上的活比起来,刘修田觉得冲车“像小孩玩水一样”。他看着苍老,头发稀疏,满脸白色的胡茬,身体却还很硬朗。但2021年满60岁后,当时的工地将他辞退了。在高强度、高风险的建筑行业,多地明确规定,“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施工作业。”
被这道禁令挡在工地外的人,大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尚未兴起时,一头扎进工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图景添砖加瓦,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工地的发展奇迹。现在,到了他们离开的时候。刘修田是幸运的,他在工地上找到了辅助性的岗位,更多的人离开了工地,只能回家干零活或种地养老。
他们像是一架高速运转的建造机器上的螺丝钉,勤恳本分地承受了几十年的重压,一朝超过了检修年限,被从机器上取下。很少有人关注他们去向何处。
这些被取下的螺丝钉,仍然卡在城市和现代文明发展的缝隙,无声地提醒着这样的事实:有一群人曾建造了城市,却很少被人关注,在过去行业还不规范的年代,他们没有充分享受到工人的福利,在行业规范之后,他们却因“超龄”而退场。
可是,他们不甘心成为闲置的废铁,别人看到的是他们身上的锈迹,而他们仍把自己当坚韧的钢,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撑起家庭的负担。

▲Z工地刚刚开始动工,正在打地基,工地对面是一排电梯外挂洋房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01
出入工地
刘修田的老家在河南信阳,从小生活在集体的环境中。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生产大队干一天活挣四工分,只能领两毛八分钱。因为穷,二十多岁了还娶不上媳妇。1984年,村里实行分田到户后,他跟着老乡外出打工,七年后成家,十年后儿子出生。
为了养家,他一年到头几乎都在外面做工,辗转于郑州、合肥、武汉和杭州的工地上。长期出苦力的身体不能歇,一歇下来,再上工的时候浑身疼。三十多年来,只有2004年到2007年三年间,他待在老家没出来。那时候妻子因肺癌去世,儿子才十几岁,父亲生病下不来床,他得回家接过照顾老小的责任。直到老人去世、儿子长大了,他才又返回工地。
当时务农的收入太低了,2007年,他种了12亩田,只得了万把块钱。村子里一半以上的人都出去了,不到65岁,很少有人会真正回归故乡。
刘修田多年打工的积蓄大部分用在儿子身上。他给儿子在镇上买了房,存了彩礼钱。2020年儿子结婚,小两口在杭州打工,一个月收入共一万多元,够他们小家庭用了。刘修田的负担卸了大半,但他还不能休息。刘修田每个月的花销在一千元左右,养老金只有一百多元。退休前,他只缴纳了三年新农保养老金,领到的金额几乎是最低一档。“我身体还很好,想挣出养自己的钱,不拖累儿子。”
满60岁后工作并不好找。刘修田不识字,一辈子都在工地上干,没有其他技能。2022年开春后,他每天去杭州杭海路劳务市场等,找工的常常有几百人,招工的只碰上十几回,无论是保安、保洁、工厂还是其他临时工,刘修田都被拒绝了,“那边年轻的、三四十岁的人也多,有的被要走了,有的嫌工资低。我不嫌弃(工资低),但人家不要。”
几天前,他才被信阳老乡介绍了这份冲车的临时工作,每天工作10小时,上午9点上班,下午4点到7点休息,晚上10点下班,一天100元。
中午11点半,另一位冲车工和门卫起身去吃午饭,刘修田坐在位置上没动,仍旧点了一根烟。他一天只有两餐,9点上班前吃早饭,下午4点回家后吃晚饭,“没钞票,混不到钱,吃少一点。”工地上的午饭12元一份,一荤一素,刘修田抽的金圣蓝色经典12元一包,省一顿午饭能抽两三天烟。

▲刘修田的工作是冲洗出入工地的土方车,以免车身泥土掉落在主干道上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劳务市场几位年纪稍大的农民工还在等机会,他们中最大的58岁。像刘修田这样60岁以上的老人在杭州的劳务市场很少见,因为找不到工作,他们大多回了老家。而五十多岁的人总想再试试,每一份坚持背后都是一段不一样的经历。
吴平五十多岁,来自江西省景德镇市。他一天吃一顿,自称睡在“蓝天宾馆”,有几分“以天为盖地为庐”的意思。2021年下半年,吴平带着3000元从老家来杭州打工,至今没找到一天活。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但他暂时回不了老家,回村需要自费隔离14天,花费几千块钱,他拿不出来。
董成从湖北来杭州打工有15年了,之前也在工地上,“工地管得严、很累,每天都要加班,赶工期。”几年前他觉得身体有些吃力,从工地上退下来,去饭店帮厨、打扫卫生,疫情后饭店生意不好,倒闭了,他又来到劳务市场。
他们学历都不高,吴平没读过书,董成读完了小学。吴平说:“我们小时候,又穷又乱,哪个去读书?”董成有些怅然:“知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有什么区别吗?脑力劳动越干越富,体力劳动越干越穷。”
说话间,两个头戴黄色安全帽的中年人从马路边走过,其中一人肩背大号蛇皮袋,跟在另一人身后走,一边听那人说话,一边点头。“这一看就是今天刚来的,跟着老乡。”董成说。
劳务市场附近有几个正在施工的工地,正对面的工地在盖住宅区,几架塔吊轮流起落钢筋,显示出工地上的繁忙。而这繁忙与董成他们无关。无论现代招聘方式变得多么数字化与信息化,建筑行业依然遵守着自己的传统,靠熟人社会拉起招工网络。
02
被冲击的熟人关系
王忠实是Z工地合作的包工头之一,现在的称呼是劳务公司老板。他52岁,进入建筑行业33年了,从工地上的小工做到“带班”(监管小工的班头),再到自己包揽项目。“清退令”的实施让他队伍里超过60岁的农民工都走了,而他的熟人圈大多“一个萝卜一个坑”,很难新招到人。陌生人是不敢用的。
“碰上捣糨糊(吴语,意指瞎折腾、惹是生非)的怎么办?不会干活是小事,来讹诈的就麻烦了。”王忠实觉得招人越来越难了,“老一代其实是干活主力军,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谁在工地上干?没有。但他们超龄了,不能用,真的很可惜。”
Z工地项目负责人对《南方人物周刊》解释,禁止超龄农民工进入工地的规定早就有了,但以前不怎么管,近几年的严格管理是从工地实名制开始的。实名登记后,超龄的问题就暴露了,而工地实名制产生之初,是为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王忠实说:“工地发工资不是按月结钱,而是按工程段或者按年结,平时就发点生活费。碰到好的老板,年底给你不少钱,碰到小老板或者工程不好的,年底跟你结不清了,或者小老板跑掉了,钱很难讨回来。”
“欠薪”曾是建筑行业的老大难问题,各级政府出过很多保障工资顺利发放的措施,要求建筑企业按月支付工资。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重点提到“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劳务费)专用账户管理制度”,要求建筑企业将农民工工资存入专户,由银行每月代发到农民工个人实名制工资卡上。
王忠实还没适应这一转变,他由包工头变成了劳务公司老板,由发放工资变成教农民工开通银行卡,用谁不用谁不能再完全由自己决定。招工难,他只能提高农民工的工资,相应地,剩下来的人得干更多的活,“加钱,加班,没有人工程也得起来,是不是?”
以前农民工从属于包工头,与施工单位没什么接触,实名制专户建立后,他们必须与施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制度与规范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同时,冲击着熟人社会式的管理。
被改变的不只是工资的发放形式。建筑工人的流动性变大了,工资年底结付时,农民工一定会等拿到钱才换地方,现在按月结清,随时可以走人。农民工的福利保障更完善了,王忠实说:“以前没有什么福利,人来了,发一套生活用品,就开始干活了,现在强制要求给工人买保险、买社保。”与此同时,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也在觉醒。
在王忠实看来,工伤保险才是建筑公司考虑禁用“超龄”农民工的关键。“工地很容易发生事故,以前没有保险,出了工伤,私下谈赔偿,严重点赔一两万,轻伤补个千儿八百的,没有什么规矩,就怕出大事情。但现在有保险公司赔,超龄农民工不好买保险,就不愿意用你了。”
“前两年清退的时候,我手下的几个人不乐意走,说‘我们不买保险行不行’‘出了事自己担’,说实话我也怕,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答应你,假如出了事我就承担责任了,公司也要承担责任。”王忠实说,他的潜台词是:谁能保证出事后真的不赔钱呢?
一个江西建筑公司的管理人员告诉《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他管理的工地上发生过一起事故,一个工人被塔吊上掉下来的东西砸死了,由于没买工伤保险,公司私下协商,赔偿了20万,因为觉得如果让政府介入可能会更麻烦,“只要农民工闹到劳动局(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去,劳动局基本上清一色判付钱的。”
王忠实介绍,被辞退的农民工,有的回家种地、有的带孙子、有的找点临时工做,跟他联系时,都说自己“心里空落落的,闷得慌”。王忠实提到他们,连连叹气,“这一代农民工,50、60一代为国家创造的财富是很多的,不管工地也好、企业也好,特别是建筑行业,国家发展得这么快,离不开我们建造的高楼大厦。”
03
充满矛盾的地方
尽管王忠实表现出非常为难又不得不配合政策的态度,但他往工地上偷偷塞过“超龄”的农民工,还曾被Z工地项目部的主管陈正发现,陈正将那名农民工请出了工地,“一看就是生面孔,再一问年龄,支支吾吾地不说话,肯定超龄了。”
陈正很年轻,一个26岁的小伙子,老家在江苏连云港,身材像壮实的北方人。他在工地上有着超出年龄的游刃有余,见到谁都能上前聊几句,被工人们喊“陈总”“领导”时,会故作严肃地回答“好好干”之类的话。
作为项目主管,陈正最主要负责的是工地上的安全问题。他需要给每一个登记在册的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告知工地危险源、风险区域和正确的安全操作,并让工人们签字确认,“事故分为两种,一种是意外,一种是责任。我告诉你了,你出事,那是意外,我没告诉你,那是我的责任。”

▲陈正看着正在打地基的工地,他戴着红色安全帽,意味着可以在工地走动监督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建筑业属于高危行业,事故多发。陈正很谨慎,经常在工地上检查,制作安全周报,里面列举着诸如“电线破皮没有更换”“氧气罐储存不当”“材料随地堆放”的现场照片。工地上如果发生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重大伤亡事故,管理人员可能会被刑拘,陈正说自己是“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
陈正所知道的上一次工地严重事故发生在2021年11月25日,一工地钢结构架倒塌造成6人死亡。看到这条新闻,陈正的第一反应是:“如果(死者)里面有超龄的,这家公司就完蛋了。”
“违反规定就算了,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但要是这人出事了,不仅停工还要罚款,相关责任人关进去。”陈正说,“现在对农民工保护得那么好,出了事舆论压力也很大。”
事实上,陈正觉得超龄农民工出事概率的确要大一点,“反应变慢,这是生理决定的,还有思想固化,他们素质普遍不高,觉得‘我这么干没事’,但事故往往发生在大意的时候。”为了提高安全性、减少事故,Z工地不仅严格禁用60岁以上的农民工,还要求55岁以上的农民工提交三个月内的体检报告。
入行几年,陈正已经摸透了工地的规则。在他看来,工地上充满了矛盾感,例如,工地的包容性很强,“没学历、没技能的人都可以干”,但工地又是严苛的,只有做到规定的工作量、规定的时间才记入考评,无论天气如何、身体状况如何;工地的流动性很大,做完一个项目就散,而工地又是封闭性的,工人的吃喝睡全在工地上,外人禁止入内。
农民工与管理人员、分包单位和总包单位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一个农民工,他的目的很简单,他可以忍受不管饭、不送水、挨骂,但是如果今天干完活没记分,他绝对不是这个态度,他的目的只是钱。而管理人员呢?希望农民工不仅干活,还得干好,还要保证安全。”
而工程分包的方式让分包单位的老板在完成工作量的前提下,有压缩成本的空间,即使现在有农民工工资专户,但分包老板可以用工程款结付一部分劳务,“超龄农民工的工资更低,这就是为什么王忠实会偷偷用超龄农民工,本质上也是一种压榨。”陈正说。
陈正也有一个疑问:“用工荒”真的存在吗?“现在我们基本上没有多少工人,以前什么都靠人工,现在机械化程度高,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不过,他认同超龄农民工转业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在等政策,比如会不会让工地给超龄人员安排辅助性的岗位。”几年过去,政策依然没有下来。
04
“超龄”的概念
如陈正所言,Z工地不缺工人,但他们的年纪普遍偏大,2022年新登记的两百三十余名农民工里,50岁以上的约占39%,40至50岁、30至40岁的分别约占24%,30岁以下的人仅占12%。王忠实觉得,随着50岁以上这一代人逐渐退下,未来十年都会面临“用工荒”的问题。
建筑业工人的老龄化远超平均值,据《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亿8560万人,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夏柱智说:“每5个农民工里,有1个还在建筑业;每4个农民工里,有1个超过50岁。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一半以上活跃在建筑业,因为他们不可能进入制造业。”
夏柱智的老家在湖北阳新县,身边有很多从事建筑工程业的人,他的博士论文以农民工为主体,研究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民工是一个伴随着中国现代化成长起来的群体,夏柱智解释:“农民工参与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同时在参与和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获得收益。”中国社会学对农村的关注,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乡镇企业、90年代中期的税费改革、1998年后的基层民主,到2005年后的新农村建设,这些课题随时代发展慢慢成为历史,而农民工始终是重点研究对象。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国家工业化后,城乡二元体制开始松动的产物,即农民可以打工了。”夏柱智认为农民工有明显的代际分化,“50、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是最早出去的一批,1982年(各地落实的时间有差异)分田到户后,劳动力被解放。那个时候比较重要的工作是挖煤、盖房子、修路等重体力活,安徽、江苏、上海的建筑业尤其多;70、80年代生的人,赶上1990年代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兴起,进厂的工作机会多;而90后的农民工,大多从事服务业或白领的工作,他们与父辈的打工经历已全然不同。”
目前,最受建筑行业“清退令”影响的正是50后、60后这两代人,夏柱智觉得用四个字可以形容他们的群体特点,他们是“吃过苦的”,“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生长在集体时代、有农业劳动的经历,那时候劳作很辛苦,没有机械、没有除草剂、没有化肥,什么都是人力。他们最先出去打工,做的也是最苦最累的活。”
夏柱智对“超龄农民工”这个说法有自己的理解:一方面,“超龄”是按照《劳动合同法》来界定的,适用于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但建筑业中存在农民工不签订劳动合同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超龄’实际上是一个管理术语,包含了一个价值判断——他们超龄了,应该退休了——忽略了农民工本身的身体状况、就业意愿和家庭收入状况,‘一刀切’了。”
他进一步表示,“农民工对‘超龄’实际上是不理解、不能接受的,他只有干得动干不动、愿不愿意干的概念,没有法律上‘超龄’的概念。”
保障大龄农民工的安全有很多种其他的方式。在田野调查中,夏柱智发现,一些大龄农民工会想办法自我调节劳动强度,几户人家凑钱买机械设备、智能设备,例如管道检测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工下地去查看管道。以往包工头组织作业时,也会依据个人的年龄状况、健康状况、技术状况和个人意愿来分配工作,“这其实是一种人性化的熟人社会的管理,而适用于城镇正规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概念(‘超龄’),不一定适合建筑业中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
到了农民工觉得自己干不动的时候,他们会主动返乡,夏柱智将此描述为“有来有回的候鸟式流动”,“我看过太多觉得候鸟式流动不人道的说法,说‘为什么我们的北京、上海、深圳不接受他们?’事实上,不是接不接受的问题,是他们不能在那个地方生活,因为成本太高了。”
05
不能老的父亲
刘修田的手让陈正想起父亲,皮肤粗糙,指甲皲裂,指节肿大,“这是一双典型的农民工的手。”

▲刘修田的手。陈正说:“这是一双典型的农民工的手”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陈正的父亲七十多岁,也是一名农民工,十几年前因为“超龄”被工地辞退,返回故乡,跟着农村建筑队干活,在村里盖房子。陈正听父亲讲过一句话:“年轻时候钱不好挣,年龄大了,钱好挣了,挣不了了。”以前在工地时,陈父一天干8个小时,工钱三百多元,在农村建筑队,一天干10个小时,工钱只有一百多元。
陈父在农村建筑队继续工作了十几年,2020年才因身体劳累而退出,但他没有歇下来,又去了绿化队,每日栽花种树,工资80元一天。陈父不愿闲下来的原因很简单,陈正还没有结婚。“我父亲算过一笔账,买房首付至少30万,买车15万、彩礼20万、婚庆10万,没有七八十万结不了婚,而我们家的积蓄只有30万,离有房有车有存款还差得远。”
即使小辈结婚,成立了自己的家庭,父辈也不会轻易退休。陈正的叔叔有两个儿子,儿子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他依然还在干,“是闲不住吗?这么说吧,老人对子女的心态就是,我还能行,就不拖累你。”
陈正见惯了这样的心态,在农村,传统伦理是如此的根深蒂固,让每一辈父母都为了子女奉献。
父亲从小让陈正好好学习,以后别上工地搬砖。陈正高考没考好,报了一所理工大学的建筑专业,兜兜转转又来到工地上。“但我也不可能因为职位便利,把我父亲带进来,不仅是规定严格,也是对他的保护。”
陈正经常对父亲说,“愿意干可以干,别想着挣钱,要保障身体健康。”但陈正知道,父亲不会听的。他每天下工后看书学习,准备多考几个证,在35岁之前当上项目经理,“成与不成,就看这10年。”但他也知道,他终究会和父亲一样回归老家。
午休的时候,陈正与刘修田一起抽烟,刘修田回顾往事,突然说了一句:“城市比农村好啊。”
“你留得下来吗?”陈正大声问,他指了指工地对面矗立的几幢电梯外挂楼房,“就这排房子,你知道多少钱一平吗?”
刘修田说:“反正我一辈子都买不起。”
陈正笑了:“七万八,你干两辈子都买不起,我也是。”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刘修田、王忠实、陈正为化名。)
原标题:从工地退场的超龄农民工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