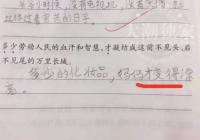【正能量】
生命的最后一刻 公交司机将车停路边救了一车人

△费红军生前不爱照相,妻子手机里的单人照还是多年前照的。
12月14日早上8点过,万州公交司机费红军所开的22路公交车经过万州区江南新区“江南一品”公交站附近时,突发的疾病让他脸色大变,身体严重不适,危急时刻,他停车、拉好手刹和断机刹(老公交车的一种刹车)、打开车门,让满车乘客下车。
乘客将已经陷入昏迷的费红军抬下车,掐人中、向120求助。120抵达现场后,对他进行了急救,不幸的是,并没有救回他年仅47岁的生命。
突发疾病,他停好车让乘客先下
万州22路公交车,有34个站,南北滨江环湖线,从“鞍子坝港口站”到“鞍子坝港口站”,全程27公里。
12月14日早上7点40左右,费红军从始发站出发,他是22路车的第二班司机,正赶上了市民上班的早高峰。“当时,车里全是人,起码有五六十个乘客,都是早上上班的。”
冯女士也是众多乘客中的一位,她说,坐车时,自己并没有发觉驾驶员有什么异常。8点过,公交车行驶至江南新区“江南一品”站附近时,有乘客在大喊“师傅,你怎么了?”
据目击者介绍,当时,费红军的脸色很不好看。“第一眼看过去,脸色惨白。”目击者介绍,再后来,费红军的脸色开始变青。
“快,打120,救他!”有乘客大声喊。司机突发疾病,大家的心中不免一颤:因为,乘客的安危都系在司机的身上。
“那一刻,我有些发呆,看到他(费红军)在踩刹车,拉手刹,直到几秒钟过后,才反应过来,司机做这些动作,是为了让乘客安全下车。”冯女士说,现场有不少乘客都目击了这一幕,费红军的刹车动作“不快,很稳”。
车停稳后,前后的大门被打开,乘客走出公交车。
也有热心乘客留在了车上,慢慢地将费红军抬了下来。在马路边,大家一边掐费红军的人中、一边联系救护车。“我们看到他的脸色,已经青中透黑了。”
冯女士还记得,下车后,不少乘客在抹眼泪,有一位大爷还哭了出来。“驾驶室附近的几个人,看到司机停车的一系列动作,在那种情况下,司机的本能反应对每个乘客来说至关重要,更何况当时前面还是一个长下坡。”
死因或为心脏方面的问题
冯女士说,她拨打120的时间在8点09分左右,接报后,急救人员很快赶赴现场,对费红军进行急救。
“这个司机有没有救活?我们想找个时间去看望一下他。”12月14日下午,在接受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采访时,冯女士问起了费红军的情况。遗憾的是,经医生抢救,并没有救回这条年仅47岁公交司机的生命。
事发后不久,费红军同班的驾驶员向万运集团万州公交分公司汇报了情况,获悉情况后,公司立即派出了工作人员,到现场辅助抢救,处理相关事宜。
“从我们接到报告,到赶到现场,也就十多分钟的事。”公司江经理告诉记者,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费红军的情况已经很糟糕,没过多久,抢救人员便宣告费红军死亡。
当班乘客,已由后面班次的车辆接走,江经理让工作人员将费红军所开的那辆车开回公司。
在开车时,车内的情况让工作人员肃然起敬。“手刹、断机刹都被拉上了,车停得很好,比我们平时停得还好。”
江经理介绍,根据有关规定,公交车停车需停在路沿50厘米以内,“他就停了这么近(用手比了一段距离),20厘米左右。”江经理说,他们觉得,在那种情况下面, 能完成这样的停车有些“不可思议”。
江经理介绍,费红军是2012年到万运集团万州公交分公司上班的,技术娴熟,服务态度好,是公司的优秀驾驶员。“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我们已初步认定费红军是工伤亡故,正在安抚家属,处置后续事宜。”
医院将于次(15)日出具相关报告,初步了解,死因或为心脏方面的问题。
“他身体挺好,怎么会说走就走了呢?”

△李女士还不能接受丈夫亡故的现实。
下午,在万州区牌楼某小区,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见到了费红军的妻子李女士。费红军家住在一个老小区里,是妻子单位分的房子,有些年代了,隔着一条走廊,一边是厨房、饭厅,一边是卧室、客厅。
“早上出门的时候,他没找到对面房间的钥匙,叫醒了我,他鞋子在对面房里。”李女士说,她晚半个小时起床,丈夫平时都不会吵醒她。费红军出门的时候,她看了一眼时钟,正好是5点45分。
李女士要给上高三的儿子做早餐,收拾家里,八点过才到单位上班。早上,她还没走拢单位,就接到了丈夫同事的电话。
“他们跟我说,要我冷静点,稳住,莫担心。并不告诉我是什么事。”李女士说,她料想,也许是丈夫出了车祸之类的,片刻过后,公交公司派人来接她,目的地竟然是殡仪馆。
直到下午接受采访时,李女士还不能接受丈夫亡故的现实。“好好的一个人,家里的顶梁柱,他身体也挺好,没觉察出什么异常,怎么会说走就走了呢?”
李女士说,费红军跟自己同年生,都是47岁,身高超过1米8,体型偏瘦,除了有点胃病,并没有其他疾病。家里饭厅的餐桌上,还放着一瓶喝了80%的“金江津”白酒,那是费红军留下的,“昨天晚上,我给他做了一桌子菜,他吃着吃着要喝酒,我没让,说第二天要开车……”李女士说,她没想到,这是自己做给丈夫的最后一餐。
费红军的母亲在医院住院,往日,李女士会在七点左右给婆婆送饭、探望。截至发稿,她还不敢告诉老人家真相,也不敢提前探望,“今天晚上,我也不敢去探视婆婆,但说好周末要去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城会玩】
英国一医生手术时在患者肝脏上“签名”:我想留个纪念
海外网12月14日电,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医院近日曝出丑闻,一名外科医生被揭发数年前在为病人进行肝脏移植手术时,以烙印方式在肝脏留下签名,被控“实际物理伤害罪”。

图为在病人肝脏签名留念的西蒙。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53岁的外科医生西蒙(Simon Bramhall)在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任职长达10年,是当地有名的肝脏移植专家。他被英国皇家检控署控告两项罪名,其中包括一项“实际物理伤害罪”。
西蒙曾于手术中在2名病人的肝脏上“烙印”自己的名字缩写“SB”。通常移植手术中的医生会使用无毒氩氦的冷冻技术来阻止肝脏出血,或者燃烧肝脏表面以勾画手术区域,但西蒙则使用氩氦刀在病人的肝脏表面“刻”出签名。西蒙行径的暴露是由于有医生在为病人复诊时,发现移植的肝脏上有西蒙的签名,于是向医院报告。英国皇家检控署表示,西蒙行为是“滥用病人对他的信任”,同时向病人施行非法武力“攻击”。病人权益组织斥责称,病人的器官并不是拿来亲笔签名的书本。
在12月13日的庭审中,西蒙对自己在患者肝脏上“签名”的行为供认不讳,称自己的动机只是为了留个纪念,对患者并没有伤害,拒绝承认“攻击”了患者。据了解,该案件将于2018年1月12日宣判。
【熬鸡汤】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

人民网微信公号消息,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
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
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

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
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
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吧。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
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
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 也好pluie 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雳,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
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和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那腥气。
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
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
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两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暗,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
至于雨敲在粼粼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
“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
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
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
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
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1974 年春分之夜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